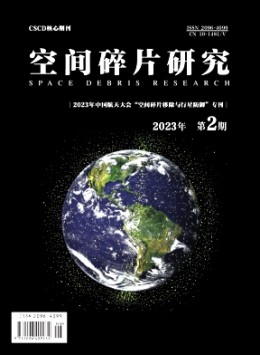空间文化理论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空间文化理论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空间文化理论真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首先应该归功于空间哲学家列斐伏尔。他从哲学反思的层面关注空间生产,结合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建立起系统化的空间理论。其代表性著作《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和《城市书写》(WritingsonCities)中,从对空间中事物的关注转向对空间生产的关注,用空间来解释社会和历史,以此来构建自己的“空间-社会-历史”三元辩证法。列斐伏尔认为,正是空间的扩张挽救了资本主义体制,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像预言的那样步入日薄西山的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更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所以,占有并生产出一种新的空间是资本主义成功的主要手段之一,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到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中而得以维持和延续。空间的再生产解决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许多矛盾,所以,空间就不限于是地理学的想象,而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和生存的主要工具。①列斐伏尔的空间认识强调的是空间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显然是和二战后资本主义全球空间重组化过程紧密相关的,是对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和列斐伏尔的社会历史层面不同,福柯无意去建立系统的空间文化理论,只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侧重对空间与知识、权力以及身体关系的考察,侧重于解读微观的权力如何体现在空间的组织和分配上。由此,地理学的隐喻在福柯的论述中不断地重复出现。他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andPunish)和《临床医学的诞生》(Thebirthofclinicalmedicine)中使用了大量的空间隐喻,如场所、城市景观、地平线、岛屿、土壤、边界线等等。在他看来,疯人院和“圆形监狱”的空间划分以及使用都表征为绝对的政治关系,并进而体现为更加严格的权力关系。所以,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空间中的“权力的眼睛”成为继意识形态之后,更加有效的规训性力量。福柯从“空间中的规训”这一角度重新解读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并进而重新组织书写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詹姆逊则是从文化的层面过渡到后现代社会的空间视域,他曾经在其代表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Capitalism)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3](16)他对空间的思考首先源于曼德尔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期,晚期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彻底的形式,它的文化背景就是后现代主义。根据这一判断,詹姆逊在总体性叙事的基础之上,将空间问题放置在后现代文化理论架构中来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此外,他结合后现代建筑美学、电影、绘画和文学来解释后现代的“空间优位”,由此空间被解读为文本,空间符号被解读为它的语法。最后,詹姆逊提出“认知图绘美学”(aestheticofcognitivemapping)来重构晚期资本主义的认知体系。
也就是要求以当前的空间概念为基本依据的政治文化模式,来理解现代空间环境,恢复批判性意识。②戴维哈维对空间议题的阐释基于两条脉络:其一,关注后现代状况下时间和空间的转型;其二,检视空间、资本、阶级和文化在都市化过程中的交互作用。他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从都市研究的角度全面地讨论了后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空间问题。现代性改变了空间的表现形式,并进而改变了我们经历和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哈维认为“空间范畴和空间化逻辑主导着后现代社会,就像时间主导着现代主义世界一样”。[1](7)后现代性是与“时空压缩”相关联的,在当代资本主义弹性生产方式下产生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人与人工制品的空间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性与一种新的“无地方性”都市环境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空间的占用、利用、支配、控制和创造成为阶级之间协商、对立、抗争的重要议题,要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就必须把握空间概念和实践的这一复杂问题。可以说,哈维借助于时空压缩概念对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体悟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些深层困境。由此看出,空间问题重要性的凸显,不只是一个学术发现,而是源于空间维度在构造当代日常生活中地位的与日俱增。索雅认为“正是这少数几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以往二十年处于霸权地位的历史决定论,这声音启动了后现代空间文化理论的发展”。[2](24)
索雅努力梳理和整合前人不同的空间理论,以此来建构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后现代空间文化理论,他不仅通过解读列斐伏尔的现代性框架来审视社会生活和空间文化之间的互文关系,而且他通过厘清詹姆逊、福柯、戴维哈维等人的一系列空间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斑驳复杂的后现代都市空间。可以说,在索雅努力继承和建立的空间哲学中,空间概念被极大地拓展和深化,它融合了“日常生活”“文化政治”“消费文化”“空间诗学”“空间批评”“景观社会”“都市空间审美呈现”等概念,并且囊括了诸如身体、城市、地区,国家和全球化等范畴,这样在索雅的理论框架里,文化身份、空间叙事、性别地理、都市审美等当代批评理论的热点问题获得了一种新的切入角度。从而,索雅所谓的“空间的生产”就不仅仅是关注地理意义上的具体对象,而是涵盖了哲学意义上的更广泛的概念范畴。
二、都市空间: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文本
伊恩•钱伯斯曾经表达过都市空间的学理意义,他认为“研究城市是一种考察世界和人类生存之谜的方式”。[6](51)从1970年城市化进程到如今后大都市的形成过程中,人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最终都是都市空间的存在者,“总是进行着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变换和生产。这一空间性的过程,开始于身体和自我的结构与行为,可以说,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7](5)从一方面上来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不断地塑造着自己周围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人们生活的社会性和集体性又开拓出更广泛的生存空间,并反过来塑造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谓的空间性其实是人类具体的生存环境或文化语境的产物。但是,都市活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所保持的优先地位一直延续在社会历史的动态中。所以,索雅的空间理论就是努力打破传统都市研究中的这种积习,他提出的“都市空间的三维辩证”思想是对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一脉相承的空间理论延续,是在21世纪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述。在索雅看来,传统都市空间的研究一直拘泥于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
第一空间的物质视角将城市空间当做物质化的“空间性实践”,强调的是“空间中的物体”,这将城市空间具体化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并细化为都市生活中可衡量、可标识的形式和实践。第二空间的精神视角是一种关于都市想象和都市虚构的构想性空间,在这里,城市空间被当做一种思想性和观念性的领域,在符号化的表征中概念化。尽管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关涉到城市空间真实和想象的两个层面,但是这种二元区分的思考模式没有表现出城市空间的真正活力和复杂性,将城市空间的特殊性简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思想等物化形式,在这种观念的直接作用下,一直以来城市空间只被当做社会化发展进程的产物和附庸。针对传统社会理论中空间分析的缺失,索雅试图在空间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更为灵活和辩证的策略。他对空间本身和空间性两者进行了区别,以此扩大了地理学的空间想象并辨识出空间问题的错综复杂性。他认为空间是一种语境假定物,而以社会为基础的空间性则是由社会组织和生产的人造空间。长期以来,不论是从机械的还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视野来看,在一般意义或抽象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都表示了物质的客观形式,时间、空间和物质是紧密关联的。这种关于空间的实质是物质的观点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一切形式的空间分析,不论是哲学的空间分析、理论的空间分析、经验的空间分析,还是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和地理景观的分析。
这种物质的空间观已经变成了一种具有误导作用的认识论基础,人们通常以此为基础分析人类空间性的具体意义和主观意义。导致的后果就是阻碍了将人类的空间组织阐释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本身也许是原始赋予的,但空间所承担的文化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索雅提倡对都市文化研究采取第三空间的视角,这样不但能结合第一、第二空间视角的长处,同时又扩大了都市文化的空间想象视野。第三空间视野的理论基础是第一空间的“真实”物质世界和第二空间的“想象”精神世界。在索雅的“第三空间”的视野中,都市空间表现为“去往真实和现象地方的旅程”,既充满幻想的乌托邦又兼顾现实性意义,既体现为个体的经验又表达为集体的感受。“理解这个鲜活的空间可以比作书写传记去解释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或者修文撰史去描述人类集体的漫长过程。在所有的这些生命故事里,完全知识是不可能的,表层下面有太多的东西尚未知晓。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完备的答案”。[8](15)面对都市空间的斑驳复杂性,“第三空间”作为最具洞察判断力的思考方式,通过对都市空间内在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介入来探索它无限的复义内涵。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索雅的空间文化理论以社会空间的三维辩证法为核心,将批判性的文化视野置入20世纪末期都市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视角中,以此在对现代城市化进程的把握上,实现了批判性文化的都市研究和传统的政治经济都市研究两种视野的融合,以此在研究倾向上产生了积极的理论互释和协同作用。
三、空间隐喻和“重构的社会马赛克”
都市是一个具有相当高人口密度的人类群体。都市空间作为人类自身创造的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要求的人工环境,首先表现为一个物质经济的实体,表现为一个现代物质环境。在现代的都市空间当中有风格迥异的建筑物、琳琅满目的物质商品、车水马龙的交通工具、五光十色的消费场所等等,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留存下来的物质形式,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明发展史,在这文明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探究具体历史环境中人的行为和意识。我们审视都市空间中物质文明的具体表现形态时,更要关注隐含在物质背后的文化因素。因此,空间隐喻被大量地拓展到社会科学的相关文献中,它作为必不可少的认知策略,起着一种解释和建构的作用。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曾在《城市发展史》中,对城市空间的文化指向给予高度的关注和评价;“城市有包含各种文化的能力,城市通过它集中的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程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了储存和复制的形式,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档案馆、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因为它不仅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是城市给人类的最大的贡献。”[9](102)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都市空间作为都市人生存和充分发展的最佳场所,是都市人格的充分体现,它映照着城市文明的光芒同时又是城市审美文化的集中体现。索雅认为,我们对都市的生活空间可以做如下的阐释:都市的新城区营造了都市的繁华和安定,都市中心使得人们充满活力,不断增加的绿色空间使人们身心放松,方便安全的医疗、社区服务使得都市生活更加方便快捷。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高耸的建筑群体使得人们的关系更加疏离,大都市缺乏个性特征,贫民窟是滋生罪恶的渊薮,城市生活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都市因为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本能而受到批判,它是建筑上的庞然大物和金钱崇拜的具体体现,是官僚机器的权力或者是金钱的社会压力的地图。正如大卫•哈维所言:“都市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场所,是一座迷宫,一部百科全书,一座百货商场,一座剧院,都市是事实和想象未必完全融合的场所。”[1](5)所以,都市文明在和科技进步共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无限的困惑。工具理性盛行于都市生活,大众消费社会使人追求物质而终被物所缚,细化的社会分工抽空了人的主体意识而使得人沦为工具。商品拜物教使得真实统一的人性自我不得不带着“人格面具”,人格的破碎和分裂也成为都市生活的常态。都市空间的营造不仅没有使人“诗意的栖居”,反而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并且伴随都市化进程的是更多难以解决的都市问题。
如果说传统的城市空间中标识的是人作为主体的日常行为,那么现代都市空间重点讲述的是汽车作为主体的故事。环境污染、噪音污染、尾气排放、交通堵塞、资源浪费、人身伤亡等问题不绝于耳。从“高速公路”对“人行道”、“步行街”的空间排挤的事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作为存在主体对都市空间拥有权的逐渐削弱乃至于丧失的过程,这也是都市空间中人的主体性精神逐步衰落的过程。不仅如此,空间女性主义批评认为,都市空间是建立在男性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的,缺乏性别差异的眼光,将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定位于“公共的男人”(publicman)和“私密的女人”(privatewoman)。而社会分工一直将性别关系定义为:男性在“公共领域”,而女性在“私人领域”。这种性别分工最终导致了空间性别关系的出现,即女性被束缚在家庭这一单一的狭窄空间,而男性则成为空间发展的主宰。同样,城市地理作为一种再现的系统,传达着一种关于人类身体的隐喻,揭示着关于男性和女性身体构造的特征,同样揭示了两性在城市和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垂直的结构通常作为神圣的“男性气概”的象征,如佛塔、摩天楼、廊柱等建筑,有些建筑还成为城市地标或者城市文化的一种象征;而住宅则反映着一种“女性气质”如诞生地、温床、庇护的子宫等。城市空间对男性来说,是“都市闲逛者”的天堂,是寻求猎奇和享乐的场所。
对于学术研究者,这种“都市闲逛者”事实上体现了一种以男性的都市体验为基础的现代性感受,他们更是被赋予整个现代城市生活和都市现代性的见证角色。这种在城市中漫游,“穿越城市,在城市的开放和内部空间里找寻冒险和娱乐;以这种方式,他创造了这座城市样貌的观念和实体的地图。在不断移动、追寻享乐、休闲和消费的过程中,‘闲逛者’成为都市再现的特定形式——他将城市再现为欲望的不同场所。”[10](111)但是“闲逛者”所必须的“移动”和“观看”的条件,在女性那里是无法实现的,“在一个父权社会中,丈夫占据公共空间而妻子占据私密空间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一个社会的危险就在于人们占据了错误的空间,尤其危险的是女性占据了男性的空间。”[11](94)她们如若重复“闲逛者”的行为,通常被赋予不道德和不名誉的联想并遭受世人的白眼,毕竟妇女是不被允许以这样的方式占据和使用都市地理空间的。针对以上的空间混乱和不平衡,一直以来反对都市化进程的声音是此起彼伏,从马克思韦伯、齐美尔到斯宾格勒,斯宾格勒更将都市化过程视为人类肌体上的癌症,其或者自行消亡或将毁灭于末日审判式的未来战争。
索雅认为这些学者对于现代大都市的未来过于悲观绝望,而持此学术立场的学者的理论视野已经不足以解读当前的都市空间,也无法深入地去辨析都市化进程中所带来的问题。索雅在《后大都市》中认为以上现象不过是“重构的社会马赛克”的必经过程,[8](349)他用“重构的社会马赛克”来描述的重点是,当今的都市空间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糅、拼贴的特征,而且都极力表明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就像一块流动的马赛克拼图,每一块马赛克代表一种文化,各种不同颜色的马赛克没有规律地拼合在一起,每一块马赛克之间都是重合的,相互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整个拼图没有所谓中心与边缘,也没有明确的边界。“马赛克”中的每一种色彩,既不愿吸纳他者,也不愿被他者吸纳。这种各自为政的“马赛克”局面,正是极力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都市空间的典型特征。索雅的空间理论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空间,他不将空间看作是纯粹的地理景观,而是将其看作是赋予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他在都市日常生活的微观文化地理和宏观叙事上的城市空间来重构后现代都市研究的概念体系,将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理论引入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都市研究中。
这种空间文化的介入并不会妨碍都市空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不会阻断都市空间的批判性想象。相反,空间文化的视野在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新的阐释和思考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视历史、社会和都市空间的共时性存在。索雅的这种都市文化分析的空间视角,关注的是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ofspace)而不是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inspace),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和理论转向,成为一种有效解读都市空间变化和发展的文化范式。而以爱德华•索雅为代表的都市空间理论的勃兴和活跃也是对当前都市文化研究和文艺空间性批评等领域的重要学术理论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