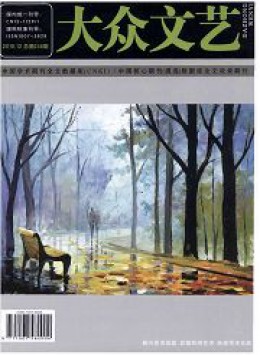费斯克大众形象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费斯克大众形象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费斯克大众形象的复杂性跟他在理论上所采取的独特定位具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大众文化研究产生了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即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两者都力图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来刻画现代大众的真实面目。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就集中体现在大众形象上。前者认为,现代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是被意识形态奴化了的对象,他们缺少主体性,失去了反抗力,因而在现代社会批判或革命活动中往往充当统治阶级的“帮凶”;后者则认为,大众是大众文化的真正创造者,他们不仅在大众文化中得到了自我认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了整个文化格局,因此,大众和大众文化值得寄予希望和重托。随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转向,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日渐式微,而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却方兴未艾。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深受伯明翰学派的影响,但同时保持着同法兰克福学派相同的理论旨趣。从理论内容和方法来看,费斯克遵循的是伯明翰学派的传统,即力图运用符号学原理来解读大众文化,从文化生产和媒介传播两个方面凸显大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费斯克强调说,“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但是,从理论旨趣来看,费斯克又并没有脱离法兰克福学派所开辟的文化批判模式。费斯克说,“同质的支配力始终会遭遇异质力量的抵制。”即是说,大众文化是对抗作为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这是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突出特点。对此,现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新秀英国的默罗比克看得很清楚,她说:“理论用不着总是把人们直接引向政治,但是在最近的文化研究领域,使我感到担心的是理论探讨变得越来越文学化和文本化,最终使我对为什么要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感到迷惑一系列问题的缺席令我吃惊。只有约翰费斯克一人讨论现实经验和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综合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各自特点,表现出一种独创性。
二、费斯克大众形象的逻辑演进
费斯克对其大众文化理论的独特定位为大众形象开辟了新的道路。一方面,他充分运用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生产理论,明确否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大众形象,另一方面他又坚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批判的路径,从而克服了伯明翰学派的自主大众形象。具体来说,大众形象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那里呈现出这样一个逻辑演进的过程:从文化生产者到文化反抗者再到日常生活者。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费斯克肯定了社会的对立性结构的存在,并且承认在这种对立性结构中,大众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始终处于从属者的地位。很显然,要消除这种对立性结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灌输法,即由精英群体向大众输送反抗意识,另一条是伯明翰学派的生成法,即在大众自身的文化活动中自动生成某种反抗意识。费斯克采取的是后一条道路。因此这里首先便会出现一个关于大众的文化生产者形象。在这一点上费斯克利用了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他说,“文化就是生产关于和来自我们的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持续过程,并且这些意义需要为涉及到的人创造一种社会认同。”这即是说,文化是一种主体性存在。由此可以推断,大众文化的主体不是别的,就是大众。而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既承认大众文化的存在,又否认大众的主体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从主体性来把握文化,这要归功于符号学的引进。卡西尔早就提出:“人是符号的动物。”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认识到符号学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只是随着本雅明和伯明翰学派的出现,大众文化的符号学研究才获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大众文化从消费性视角到生产性视角的转换。我们看到,费斯克的文化定义中的“意义”和“认同”这两个关键词本身就表明了大众是一种符号化的主体性存在。应该说,从消费性视角到生产性视角的切换,对于理解和把握大众和大众文化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大众不再是某种文化的被动接受者或消极消费者,它还是自己文化的积极创造者和传播者。
一句话,大众是大众文化的主人,大众文化的出现表明了大众的主体性显现。但是,仅仅把大众文化当作大众主体性的显现,这并非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根本目的。前面我们说过,大众始终在社会的对立性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创造自己的文化,绝不会自娱自乐,它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反抗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大众本身是属于从属地位的人群,这种从属地位决定了他们将始终处于一种既清醒又痛苦的状态中;第二,大众本身在权力或资源上的缺失使得大众在减少痛苦增加快乐上的选择不可能太多,由于文化所涉及的是意义的生产,因此它将不可避免地被大众越来越多地加以利用。因此,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中的大众必然是以反抗者的身份出场,并且这种反抗还不是消极反抗,而是积极反抗。费斯克说:“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涉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这些意义是有利于从属者的,而非支配性意识形态所喜欢的那种。”当然,无论大众从消费者转为生产者,还是从生产者转为反抗者都并不意味着大众在现实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发生了改变。但是这种从属者地位并不决定着大众在文化领域中会无所作为、任受摆布。实际上,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虽然不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但却具有侵蚀和颠覆的作用。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大众文化中找出和确证大众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微观政治效益。费斯克用了大量例子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比如,他指出,现在的电视节目包含着大量的娱乐节目,尽管这些节目有些确实是很无聊而且庸俗,但是意识形态不得不作出了让步。费斯克指出:“现在很少有人相信控制民众的娱乐以提高他们的品味会对国家有益。”再比如,关于麦当娜现象,费斯克说,“麦当娜是个物质女孩,但同时也是符号。”她代表着现代女性对父权或男权的一种抵制态度。因此,尽管在宏观政治层面上有足够理由来拒绝她,但是在微观政治层面上来说这样做就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一来,会流失很多选票。费斯克特别反对法兰克福学派那种危言耸听的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可能达到控制大众思维和意识的目的。另外,他也反对那种认为掌握了技术就可以随意操纵大众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当然可以被解读成支配性的或压制性的,但是这样一来,它也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如果联系到前段时间在我国上演的“3Q”大战,应该说,费斯克的理论还是很有说服力。
费斯克有时候用“游击队员”来称呼大众,实际上,现代大众比“游击队员”更具有进攻性,因为它是无形的而且整体作战。因此,费斯克说,“大众文化政治在微观层面上比在宏观层面上要更有效且明显得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把大众从宏观视角下解脱出来,大众的真正形象也就必然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因为,只有通过日常生活的分析和批判才能理解大众和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效益。费斯克坚决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路线,但同时也反对伯明翰学派那种把大众沉沦于日常生活的做法。在他看来,大众的日常生活始终跟政治斗争相联系,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费斯克说,“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矛盾的利益不断得以协商和竞争的空间之所在。”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消费(包括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获得生活资源,同时也是区分和建构不同主体的重要标志。费斯克说:“当商品为老板们效力完毕后,它从资本主义的战略中撤身出来,开始成为日常生活文化的资源。”因此,消费本身变了生产,并由此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反抗。费斯克把大众形象定义为日常生活者具有双重用义:第一,他希望为大众和大众文化获得一个更广泛的同时又是合法的反抗空间;第二,他已经认识到从意义和符号本身来进行反抗必定会虚弱无力,要突破这种局限性就必须重新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在日常生活行为特别是消费行为中真切地把握到大众反抗的原动力。
三、费斯克大众形象的“缺失”
不可否认,无论是文化反抗者,还是日常生活者,费斯克的大众形象定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非是假想的凌空构想。正像在生产体系中一样,随着资本控制的加剧,反资本的因素必然也会加剧。在文化系统中也是如此。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反抗因素,费斯克则力图在资本主义文化系统中发现反抗因素。这一理论探索本身极富开拓性。但是由于费斯克对这些反抗因素的把握并不是基于生产关系作出的,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他在大众形象的把握上出现某些“缺失”,表现如下:
第一,费斯克大众形象虽然赋予了大众以“话语权”,并且这种“话语权”通过大众文化确实可以部分实现出来,但是对于大众来说,或者说对于广大的“从属者”来说,并不仅仅只为“讨个说法”而满足。因此,大众对大众文化的诉求并不是停留在意义或符号上。
第二,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只注意到了大众形象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它的消极的一面。他没有看到大众文化本身的良莠不齐,而一味的对它们表示认同和肯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为那些有背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大众文化进行辩护,这是极不应该的。
第三,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在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把握上出现了偏差。他没有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没有看到执行这两个功能的主体往往是相同的,忽视了对生产结构即生产者与所有者的分析,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大众形象有乌托邦的倾向。
总之,费斯克继续遵循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进行大众形象纠偏,一方面坚持把文化作为政治斗争的场所或工具,另一方面又力图从大众本身出发寻找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动力,为大众文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