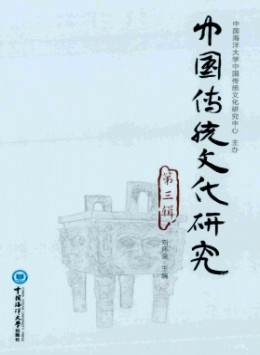传统文学论文:分析天赋与俄罗斯文学传统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传统文学论文:分析天赋与俄罗斯文学传统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本文作者:邱静娟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纳博科夫于1937年创作完成并推出《天赋》并非偶然,这一年正值他衷心热爱的诗人-作家普希金离世100周年。纳博科夫此举是作为对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献礼,也是“最为公开地向现在和过去侵害普希金宗旨的行为发出了挑战”[4]70,以批驳巴黎俄侨文学“数目派”对普希金的无知和虚无主义态度。小说鲜明地表达了纳博科夫对普希金的崇敬仰慕之情,以及他坚定继承普希金传统的决心,确认并维护了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崇高神圣的地位。作家依照对待普希金的态度来衡量俄罗斯批评家的优劣,更重要的是,借文学青年费奥多尔勤奋学习文学传统(尤其是普希金传统)以发展壮大自己文学天赋的流亡生活,普希金的文学遗产多次出现在《天赋》中,它们或是普希金作品的引文、题词、主题,或是能引人联想到其作品的相似物,或是对普希金艺术手法的发展等等,不一而足,普希金由此成为这部多主题小说的主要主题,并与费奥多尔寻父的主题交融在一起。纳博科夫让读者感受到了普希金生机勃勃的气息,领略到这位俄罗斯民族文学奠基人的恒久魅力。作家为笔下男主人公取名费奥多尔•戈都诺夫,它或多或少与普希金的作品(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相联系。纳博科夫同时让费奥多尔的保姆来自与普希金的保姆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相同的地方。小说第一章展示了费奥多尔诗歌学徒期的部分诗篇,它们都依照四音步抑扬格书写而成,这是由罗蒙诺索夫创立、并经普希金之手使之不朽的韵律。费奥多尔对文学道路上的对手孔切耶夫暗怀类似沙莱里的妒忌心理(普希金的小悲剧《莫札特与沙莱里》),想象只有用毒酒方可遏制对手的天资(当然,这只是费奥多尔心地卑劣时的想法,后来,已经成熟自信的费奥多尔与孔切耶夫成为文学上的知音)。费奥多尔还通过假想的对话表达了对普希金的敬意,确认并维护了后者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宗主地位。第二章是费奥多尔对父亲的回忆。戈都诺夫•切尔登采夫的普希金主题与父亲的主题基本吻合。费奥多尔受普希金作品的启发,想象出追随父亲———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和旅行家去中亚和中国的旅程。费奥多尔早就有意写一部与父亲有关的作品,只是时机尚未成熟,阅读普希金的散文,激发了年轻诗人的创作力,也使他找到了适合自己天赋的文学体裁,他从写诗转向写作散文。在揣摩散文创作艺术的过程中,费奥多尔把普希金的作品当成学习的范本,继而把现实生活与普希金作品、父亲与普希金混淆在一起。因此,父亲的形象其实融合了父亲本人和普希金两个人物。费奥多尔想象中的中国之行,可看作是纳博科夫对普希金和自己曾怀有的梦想的补偿。第三章是费奥多尔被迫搬家,他从研读普希金作品转向学习果戈理作品。柏林的俄罗斯侨民和当地居民给费奥多尔提供了“庸俗性”的绝佳样本,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庸俗人物,他的新居生活是一次发现“庸俗性”的旅程,而果戈理的艺术则为如何嘲笑“庸俗性”树立了榜样(在《尼古拉•果戈理》一书中,纳博科夫挑出“庸俗性”作为果戈理艺术攻击的主要目标),纳博科夫让年轻的作家费奥多尔继承了果戈理的艺术成果———嘲讽庸俗。但甚至学习果戈理的主题仍然多少与普希金有关,因为是普希金首先发现了果戈理讽刺庸俗的才华:在《关于<死魂灵>的第三封信》中果戈理写道:“外界对我有不少议论,在分析我的这个方面那个方面,但没有人指明我的主要的本质。唯有普希金一人早有觉察,他总是对我说,还没有一个作家具备这样的才能,把生活中卑下庸俗的品质表现得这样鲜明,把卑劣者的卑下庸俗之态刻画得这样有力,使得那些极易在眼前滑过的细微之处能在大家眼中呈现为庞然大物。这就是我所独具而为其他作家所缺少的主要禀赋。”[5]151-152很明显,费奥多尔实际是透过普希金的蒸馏器汲取着果戈理的精华。第四章是费奥多尔滑稽模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记。这里,费奥多尔用果戈理的手术刀,对传主这位自由知识界的宠儿施行了残酷而有趣的活体解剖。在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革命民主主义者以普希金的《现代人》作为主要论坛,开展反对纯艺术的运动,旨在推翻普希金的权威地位。因此对崇尚纯艺术的费奥多尔(维护艺术的纯洁也是纳博科夫的信念)而言,普希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了俄罗斯文化史中两条对立的路线,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了美学上的功利主义,对普希金的评价是他最脆弱的部位。费奥多尔对这位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进行恶搞,并称其为“参观阿佩里斯画室的靴匠”,这个评价来自于普希金1829年创作的寓言诗《鞋匠》:鞋匠对画家的作品指手画脚,画家最终忍无可忍,让他别对补鞋外的事横加评论。费奥多尔以此来嘲讽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懂艺术。《天赋》里费奥多尔的传记被拒绝发表,纳博科夫《天赋》的第四章同样被俄侨杂志禁止发表,其原因都是因为蓄意嘲弄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最进步的人士。但费奥多尔比现实中的纳博科夫幸运,他的传记虽经波折却很快出版,《天赋》完整的版本却是此书创作完成十几年后才得以在美国问世。纳博科夫认为这是“生活不得不模仿它谴责的艺术的一个绝佳的例子”[6]413。作家可能预见到作品所要遭受的命运,好像要预先采取防止删除的措施,在第五章中对被清洗的章节加以戏拟式的评论,评论嘲讽了评论者学识浅陋。这种技巧就像普希金当年所为,他在《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第二版前言中没为自己辩解,却复制了某些对他的作品所作的评价。费奥多尔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态度:在宴饮狂欢中微笑着迎接死神,使人联想到普希金的《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天赋》结尾的段落以在韵律上模仿奥涅金诗节收束全书。对普希金传统的学习、借鉴、利用、改造与评价贯穿了费奥多尔的整个学习成长生涯。因此,阅读中读者始终能够真切感受到这位早已辞世的诗人活生生的存在。普希金仿佛从来未曾离开,在他暂时隐去100年之后,在纳博科夫的《天赋》中,普希金归来了!
针对果戈理的影响问题,1966年纳博科夫在答记者问时说道:“我那时很小心,尽量不学他。作为一个老师,他疑点很多,很危险。”[7]106其实,对纳博科夫的一面之词读者尽可不必完全相信。早在纳博科夫俄语创作时期,就有侨民批评家发现了纳博科夫与俄罗斯讽刺大师果戈理、谢德林在创作上的共同性。自传体作品《天赋》更是暗示了作家对果戈理讽刺艺术的学习。在费奥多尔的学习生涯中,果戈理这位俄罗斯文学的散文之父,是他继普希金之后要借鉴的一个重要对象。《天赋》第三章描述了费奥多尔学习果戈理的经过。费奥多尔借着《死魂灵》的翅膀,踏上了发现庸俗的旅程。路途终点,他已是一名初步形成自己风格的作者了。费奥多尔以果戈理为典范,学习借鉴果戈理的讽刺艺术,嘲讽了各种庸俗,后来,他还接过前辈作家的手术刀,对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了“活体解剖”(费奥多尔认为车氏误导了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综合并发展了白银时代作家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观点,把果戈理和他的作品从社会历史批评的模式中解放了出来。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完全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也完全不是忠实反映生活、暴露生活中一切腐朽丑恶和不合理现象的现实主义杰作,“把他的戏剧当作社会讽刺和道德揭露作品意味着错过了它主要的东西”[8]59,“在《死魂灵》中寻找真正的俄罗斯现实生活是无益的”[8]78。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纳博科夫有意忽视了果戈理作品大量的现实内容,而认为他的世界是由众多次要人物组成的“梦幻世界”[8]68,他的作品充斥了形形色色这样的人物,在戏剧中,这些次要人物由出场人物提及;在小说里,果戈理通过“各种补充说明、隐喻、比喻和抒情插叙使小说中的次要人物活跃起来”[8]83。这些次要人物,有些是作者创造出来、在作品中存在但从未出场的,还有一些人物是由作品中的人物杜撰出来的,“他们不是影子,而纯粹是幻影了”[8]64。他们不具有情节意义,经出场人物提及后,在后文中绝不会再出现。果戈理无疑有别于契诃夫必让悬置的枪走火的精简手法,而纳博科夫认为次要人物的魅力就在于“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现实化”[8]61。纳博科夫指出,果戈理的梦幻世界也不是完全与现实生活绝缘,它的道德内涵是对庸俗的批判。“指斥什么为庸俗,我们不仅作出了审美的评断,还建立了道德的法庭。”[8]388庸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恶习”,在纳博科夫眼里,它是“假理想、假同情和假聪明。欺骗是真正的市侩的忠实同盟”[8]385,“俄罗斯自从学会思考以来,所有受过教育的、敏感的和自由思考的俄罗斯人,就深深领略过它的贼头贼脑和纠缠不休”[8]73,“在与俄罗斯有紧密联系的民族中,德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儿不仅不嘲笑庸俗习气,它还成为民族精神、习惯、传统和社会氛围的一个主要品质”[8]73-74,纳博科夫还从歌德的《浮士德》里嗅出了庸俗的气息。纳博科夫认为《死魂灵》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百年前,当由黑格尔和施勒格尔(加上费尔巴哈)调制的醉人的鸡尾酒影响彼得堡的时评家时,果戈理在那篇故事里,用自己巨大的天才顺带提及了渗透德意志民族的不死的庸俗的幽灵。”[8]74纳博科夫还从文学作品中开据了一连串的庸俗之徒,并指出在果戈理的梦幻世界里也不乏这样的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死魂灵》中有一些傲慢的死魂灵存在,他们是市侩”[8]78,如乞乞科夫。这样,纳博科夫自出机杼地解读了果戈理的作品,并为自己的作品寻到了传统的“根”。《天赋》里,果戈理讽刺艺术的种子在纳博科夫的作品里发芽生长,最终枝繁叶茂。在第三章,纳博科夫借果戈理艺术的东风,让读者见识了俄侨眼中德国社会生活里的“当代死魂灵”。费奥多尔通过学习果戈理,获得了果戈理式的慧眼,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庸俗分子(次要人物),又用果戈理式犀利的手笔,撕下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庸俗的本质。这些人物除了直接出场的外(济娜的母亲和继父以及费奥多尔的一些熟人),大部分人是由济娜提及的。在本章结尾部分还有从一个作家那里脱口而出的虚幻人物。他们正如果戈理笔下的次要人物一样,一次出现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但这不妨碍他们在作品中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为了表现一位叫特拉乌姆的市侩(他是济娜所工作的律师事务所的几个雇主之一),纳博科夫所用的笔法就完全是果戈理式的。作家把他所理解的庸俗的种种表现诸如自高自大、自私虚伪、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老于世故等,都集中在这个酷似半轮月亮的矮子身上。而且纳博科夫塑造的这个走样的胖子,还多少具有了乞乞科夫的特点。
《天赋》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它是“文学百科全书”[2]147,涵盖了十九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和纳博科夫创作的几乎所有主题[9]189,同时它也是“一部独特的教育小说,描写了艺术家创作的成长过程”[2]147,它叙述了俄国青年作家费奥多尔在旅居柏林三年多的时间里(1926,4,1-1929,6,29)创作才华的发展和成熟。小说结尾,虽然费奥多尔计划中的写作尚未付诸笔端,但他此时已经具备成为大作家的潜质,他还预见到了小说的成形,对完成作品充满了信心。纳博科夫借费奥多尔的学习生活告诉读者,作家的才华并非天赋,才华是天才加上刻苦学习传统,继承、借鉴并超越传统的结果。《天赋》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虽然纳博科夫一贯厌恶把作品中的人物与自己混为一谈,但俄侨批评家还是很快从费奥多尔身上发现了作者的影子,纳博科夫本人也在《天赋》一书和英文版前言中含蓄提到作品和自己的关系。可以说,虽然不能完全把主人公与纳博科夫等同起来,但费奥多尔文学才能的成长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创作历程,费奥多尔所表达的文学观念、他对俄罗斯诗人、作家的评点则可以代表纳博科夫本人的观点。这些可从纳博科夫的自传、访谈录和文学讲稿中得到印证。纳博科夫灵活地运用多种文体来表现费奥多尔作为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大体相应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轨迹:第一章展示了费奥多尔《诗集》里的诗歌和青年诗人的创作热情和过程,他的诗歌创作时期对应于以普希金诗歌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第二、三章费奥多尔转向散文创作,他的散文学徒期对应于俄罗斯文学的普希金果戈理时代,他首先模仿普希金的韵律散文,然后学习果戈理的讽刺艺术,这部分的语言风格也由诗意抒情转向揶揄讽刺;第四章费奥多尔为批驳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实用主义文学观念,以车氏作为靶子,举起果戈理讽刺艺术的火枪开火进行文学射击训练。纳博科夫对这位批评家持双重态度,他既钦佩车氏为公众利益的献身精神,又鄙弃他的文学实用主义,因而该章语体时而崇高庄重,时而讥诮挖苦;第五章费奥多尔在经历传统的洗礼后,迈进现代。于是本章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形式手法表演的舞台。费奥多尔对文学传统博采众长,去伪存真,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凭作家和批评家对普希金的态度来裁决评断他们的优劣,而且把他的每一个艺术成就都放在普希金的天平上来衡量。“普希金,他的生活和创作被认为是《天赋》的音叉。”[9]190《天赋》第一章费奥多尔借假想的谈话,评说了俄罗斯文学的成败得失,捍卫了普希金的崇高地位,表达了决心维护艺术纯洁的态度。谈话同时反映出未来作家对传统孜孜以求的态度:以一流作家为榜样,兼顾其他。这也是纳博科夫本人的立场。《天赋》中历数了大量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和诗人的优劣,还有对俄罗斯文学界和批评界知名人物的暗指或影射。俄罗斯作家还走进《天赋》,成为小说的人物,书中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并存,这些人物成为费奥多尔学习、缅怀或抨击的对象。“作者公开从19世纪散文汲取养料,直接用它充实自己。”[9]189小说第一章描写费奥多尔以诗歌起步,后转向散文。费奥多尔首先以他崇拜的普希金为老师,对传统狂热的学习热情甚至使普希金渗入到他的生活,他把普希金及其作品与现实混淆在了一起。后来费奥多尔被迫迁居,他从诗意的超现实坠入充斥形形色色庸俗的人世间,新居的环境庸俗不堪,新居的生活成为庸俗性的发现之旅,流亡者版的《死魂灵》则是旅行者的指南。掌握了果戈理的艺术后,费奥多尔用这把利器来抨击与普希金艺术观点相左、自认为是遗毒深远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写作传记,费奥多尔博览群书,钻研19世纪6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学习传统积累知识的过程里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随着《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的面世,吸收了传统精华、被传统充实提高的费奥多尔已经作为一个成熟作家浮出水面,他正酝酿着一部新的作品……相应于费奥多尔学习俄罗斯文学传统促进了自己创作才能的增强,纳博科夫在《天赋》中大规模引用文学作品,使其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对文学传统的有效借鉴利用充实了作品的肌体。这是纳博科夫艺术创作的重要方法和技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普希金作品的形象、结构、思想、语言等被密密地织入《天赋》:“在《天赋》第二部分的档案资料中,男主人公说,流亡的使命在于把父辈的赠品传给后代。这样的赠品首推普希金传统。”
在觅得普希金的珍藏后,费奥多尔(或者说纳博科夫)的文学探险之旅并未就此止步。果戈理、丘特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别雷等,都是主人公和作家在探险历程中挖掘的宝藏。旅程的终点,费奥多尔作为作家的创作才能日趋成熟和完善,纳博科夫则为俄罗斯文学传统谱写了一曲深情的赞歌。如果说,祖国文学的传统陪伴费奥多尔走过生命中最阴暗的日子,支持了他文学天赋的成长,主人公的创作道路表明:才华并非天赋,对文学传统的学习是作家成长的基础,那么“对纳博科夫而言,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是帮助他确定自己创作和生活道路的基础”[9]188。纳博科夫在《天赋》篇首题词“忆母亲”,就充分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款款深情、挚爱、依恋和感激。“只有在《天赋》中纳博科夫才完全表达了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忠诚”[9]190,“19世纪的作家留给他的文学世界,经过分散、丰富、重新认识和发展选题,影响了他虚构的形象”[9]188,“作家把引证作为方法,公开使用别人的言辞,就像自己的一样。他不能拒绝天才的前辈作家”[9]189,“引证充满了小说的所有层面———情节、风格、思想。……19世纪文学的例子扑面而至,作家仿佛信手拈来”[9]190。虽然《天赋》鲜明地体现出纳博科夫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亲缘关系,但是纳博科夫没有跟在传统身后亦步亦趋,他充分吸取俄罗斯文学在经过19世纪辉煌发展后积淀的丰富多样的经验,进行加工、改造和完善的基础上,实现了自己的创新追求。小说结尾主人公费奥多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纳博科夫也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风格———超越创新。承载着厚重传统的《天赋》没有被传统的光晕所遮挡,它焕发着作家创新的光辉,“《天赋》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领会19世纪俄罗斯文学风格经验基础上的新的诗学形式”[9]189,《天赋》是作家对自己在学习传统基础上所做的创新的回顾和总结。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