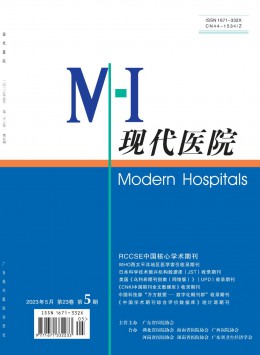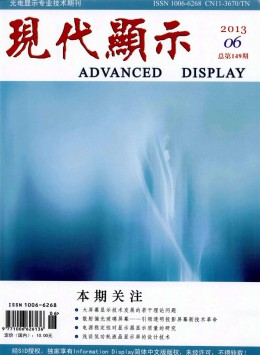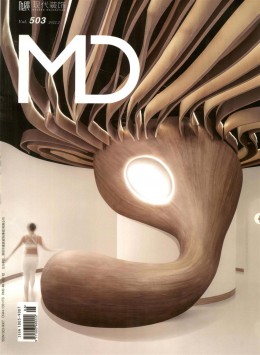现代循环农业的兴起与反思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现代循环农业的兴起与反思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传统农业生产中的生态循环观及实践
中国有几千年悠久的农业文明,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农耕制度和农学思想,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传统农业生产中的生态观和循环观。循环观认为宇宙万物循着环周进行周而复始永不停息的运动,任何事物的产生、成长和消亡都是循环运动的表现,各个具体事物及其运动只是循环运动中的一个纽结,循环是一种自然社会运作的普遍机制和规律[1]。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长盛不衰、源远流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这种生态循环观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经营思想上,更体现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传统农业生态循环观的建构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这一理论基础和农业生产过程这一实践基础。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的精髓就是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三才论”架构下的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观。“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亲和、共生及一体性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与中和,主张以天、地、人、物相合相融的整体思维方式建构自然社会系统。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及传统哲学的主线,也是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传统农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总结出与传统哲学思维相匹配的农耕制度和农学思想,如农业生产要遵循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要遵照自然规律,协调农作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成为传统农业生态循环观的实践基础。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农业生产实践共同建构了农业生产的生态循环观念,并不断应用到具体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去。传统农业中的生态循环主要包括2个层面,一是价值理念层面上的循环观,二是农业生产中的循环实践。传统农业中的循环观和循环实践相辅相成、互相强化,循环实践来源于传统农业的循环观,循环观指导农业生产的循环实践;同时,农业生产在具体的实践中又不断丰富、完善传统农业的生态循环观。
1.传统农业生产的循环观
传统农业是我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民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和基本的收入来源。一方面,基于农业的重要性,农民大都祖祖辈辈固守在土地上,循环往复地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基于农耕实践对土地和农作物等自然资源的依赖,农业生产必须依赖时间节律、气候以及自然生态演替规律,进行周而复始的循环耕作。这是传统农业生态循环观产生所面临的客观现实。首先,传统农业的生态循环观体现在农民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传统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和“谷”,农民从生到死、从早到晚都要长期固守着一块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美国农学家金在1909年考察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农民后,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人成为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他们的农业不是和土地对立的农业,而是和谐的农业”[2]。农业活动的循环体现在一年四季的交替中,它忠实地反映和遵循四季的自然变化。与工业以无生命的材料为劳动对象不同,农业的对象是有机的生命体,是在复杂的环境下处在不断循环中的生命体,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是世代循环的。其次,传统农业要围绕时节、气候等自然环境而周而复始。传统农业生产的过程就是种子-植株-种子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具体包括了农作物的播种、萌芽、生根、长叶、开花、结实等环节。农民要按照二十四节气的变换来安排生活,指导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过程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要关注自然物候、四季更替、气候变化和日月星辰的位置移动,农业生产要跟农时、季节对应起来。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循环节律,同时又要和宇宙大系统的循环节律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丰收。我国自古以来就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以“物候”“时候”为基础,以“农时”为核心的精耕细作农业传统。夏代历书《夏小正》按月份把天象、物候、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年年如此,循环往复。在这里面,中国祖先就已经认识到要把天地宇宙的大循环与农业生产、农事活动的小循环联系起来,并认为人类生产活动的时节安排与宇宙自然的节律周期具有同比性和同步性,这奠定了传统农业生产循环观的思想框架。另外,《诗经•豳风•七月》《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礼记•月令》等都曾列出每个月气候、物候和农事等,即以物候定时节,以时节安排农业活动。因此也产生了四季、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等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节气知识[1]。农家“月令派”也坚持以“农时”为核心,以岁时季节来安排农事活动。人们处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其自然地理、四季节律、气候物候循环变化都关系到农业生产实践,农业生产、农民生活都围绕着四时节律来循环往复。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也提到了“农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时间季节循环对于人们现实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间的辨认不是处于哲学的考虑抑或好奇的结果,计时不仅是生产实践的需要,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需要”[3]。几千年来,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始终坚持“顺应天时”“不违农时”的准则,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农业生产按照天时、物候等自然规律进行运作的循环观念。
2.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循环实践
循环观是指导传统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理论基础,同时又不断影响农业生产的具体实践。在长期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传统农业将循环观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循环实践和稳固的农耕制度,如水稻栽培、旱作农业、蔬菜、牧草、绿肥、果树、经济植物、水产、禽畜、野生生物及其遗传多样性彼此之间的巧妙组合等,这些都是经过人类长期栽培、选择和适应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强调物质循环利用本质上是提醒人们在农业种植过程中,注意利用其他各业以便维护土地的生态质量[4]。第一,轮作轮耕是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经历了几千年来耕种方式的演化进步。就轮作而言,从原始农业开始就已经出现年年易地、多年循环的撂荒耕作和连耕、连撂的轮荒耕作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创始了轮作复种制。随着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的发展,土壤耕作也相应地采取了翻耕和免耕或耨耕相结合的方式[5]。轮作轮耕的种植制度实际上正是遵循了农田循环利用的思想,轮作轮耕是农田进行休养生息的重要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使得土壤肥力不至于降低。第二,土壤改良中的循环实践。中国农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几千年来,中国土地的地力没有衰竭,而且很多土地的肥力还越种越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地力常新壮”的耕种思想,“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6],即认为土壤可以通过改良的方式来保持地力,在这种条件下很多瘦瘠的土地都陆续被改造为良田;二是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生态施肥思想,金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在于中国农民勤劳、智慧、节俭,善于利用时间和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并以人畜粪便和一切废弃物、塘泥等还田培养地力[2]。中国传统农业是一个物质封闭循环的结构系统,几乎所有的副产品都纳入到了循环利用的过程中去,从而弥补了农田养分散发的损耗。农民“把一切可利用的废物变成肥料返还给土壤,犹如自然生态系统的枯枝落叶归根还给土地变成养分,实现生物质小循环一样,从而能维持地力长久不衰”[7]。
传统社会中存在众多变废为宝的材料,如作物秸秆、人畜粪尿、灶灰炕灰、烂菜叶果皮等有机垃圾,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农家肥的种类基本上包括了生产生活中所有的废弃物,甚至在空间上突破了农村的范围,将城市所产生的粪便、垃圾等返还到农田中去。通过废弃物质循环再利用,实现无废弃物生产,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特征。“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地,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寂、粟阁”即是这种写照[6]。农民将废弃物还田大致由3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在每年春耕之前,农民将会集中时间将人畜粪便等运到田间地头,等到耕作田地时就可以直接将粪便掺和到土壤中去作为“底肥”,这一部分是农家肥肥田的主要部分;第二部分是在农作物成熟之前,主要是农民将生活中的灶灰坑灰、烂菜叶果皮等不定时地返还到田地中,被称为“追肥”;最后一部分是在每年秋收之际,农民将剩余的植物秸秆等直接留在田地中让其腐化到土壤中去,以增加土壤肥力。为了解传统循环农业,课题组于2012年11月对北京市延庆县小浮坨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访谈。小浮坨村位于长城以北3km,行政区域面积395hm2。在农业生产上,小浮坨村遵循了同样的循环规律。在合作化以前,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养殖一些禽畜,如猪、牛、羊、驴、骡子、鸡等,养殖的目的主要用于生产农家肥。将禽畜粪便运到田地中后,还要掺上一些荒土以增加粪肥的数量,为了达到平均施肥的效果要将粪肥均匀撒放到农田去中。合作化之后,集体土地用肥主要有2个来源,一个是沤肥、绿肥,生产队在每年青草茂盛的时候会组织社员到山上割青蒿子,然后用马车运到田地中提前挖好的坑中,将青草和水掺到一起干沤,以此制成沤肥、绿肥。第二个来源是农户家中的人畜粪便,除了留一点用于自留地外,农户每年都要给生产队上交粪肥,这成为集体化时期农田肥料的主要来源。在家庭承包经营后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村民仍旧延续了传统生产习惯,那就是养殖禽畜以获取农家肥。小浮坨村村民一般每户要养2头猪,有的还养驴和骡子,大部分农户都养10只左右的鸡。
通过养殖这些禽畜,农户不仅可以满足当时对肉、蛋的需要,饲养大牲畜还能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农民更看重的还是能获取大部分农田生产所需要的肥料。对农家肥的重视,还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的话语中,如“种地肥当家”“肥水不流外人田”等。通过这种方式,农民就可以在有限的资源中实现高效的循环利用。首先,农民将禽畜粪便全部施加到农田中去,不仅避免了动物粪便对村庄环境造成污染,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提高土壤肥力和粮食产量的目标,也就是农民所说的“猪多、肥多、粮多”;另一方面,农民养殖禽畜并不像现代规模养殖需要专门的饲料,而基本上依靠自家粮食加工后的糠皮、麸皮、山坡上的青草、野地里的苦菜等,剩菜剩饭、刷锅水等也都是养猪“泔水”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养殖家禽家畜在当时具有较小的生产成本。这种循环利用实际上体现的是种植业和养殖业两者之间在资源、能量上的交换和平衡,而使用绿肥和沤肥体现的是种植业和自然资源之间的能量循环。此外,很多农村还将养殖业与渔业结合起来,即在鱼塘周边搭建鸡棚或猪圈,这样就直接可以用猪粪或鸡粪来喂鱼,塘泥等又可以返还到农田中。总之,传统时期农业生产过程充分尊重和利用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利用的自然规律,并且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了自然循环的良性系统。
传统农业循环结构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当前,传统农业中形成的农业循环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发展的思路不再依靠农业内部或村庄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传统农业循环观和循环实践逐渐退出农业生产的历史。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加,特别是设施农业的兴起,农业生产突破了时节、物候限制,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种植模式。另外,农村社会中的生态施肥思想也被投入产出的经济核算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使用人畜粪便、秸秆堆肥、灶灰坑灰等有机肥,而更多的使用化肥,这就使得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的能量循环走向终结。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通过使用农家肥、青肥、土地轮种、套种、灌溉、修建梯田等多种方式,基本实现了对土地的永续利用。而在现代社会,农业生产过多地依赖化肥和农药,土地在短短的30多年间就已经出现了硬化、板结、地力下降、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8]。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传统循环农业的终结?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农民循环观念的变化。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一方面要固守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到农作物自身“种子—植株—种子”的生长节律和自然地理、四季节律、气候物候的循环节律,农民必须为应对这一周而复始的过程而在农业生产生活上做好适应性的安排,这就强化了循环往复观念。而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生产已经很少关注天时、地宜因素。虽然在总体上还是春耕秋收,但是在具体的耕种环节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开始凸显出来。如顺应动植物生长规律的农作制度被现代科技所改变,大棚技术使得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和周期可以不再遵循天时、物候等。也就是说,现代农业生产实践使得农民在几千年来形成的循环观念不断弱化。第二是轮作轮耕和间作套种等种植制度的变化。合理的轮作轮耕和间作套种是传统农民保持土壤肥力的好办法,而在当前很多农村,农业只是农民收入来源的兼业和副业,所以农民就不愿意在农业生产上花费太多时间。“很多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只是播种时回家看看,把种子撒到地里,或请人帮助播上种,然后就一去不复返,施肥、锄草、灌水等一应投入均免掉了”[9]。为了节省时间、减少麻烦,农民种植单一作物,没有了以前的间作、套种以及多种作物、蔬菜的种植。北方的很多农村在农业生产中都由以前的一年两熟改为一年一熟,南方农民则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这就使得土地的能量循环过程发生改变。第三是传统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循环系统发生改变。农家的畜、禽、鱼、桑、蚕和菜地、农田、鱼塘、树林、村落等可以构成一种和谐的农业循环生态系统,禽畜粪便可以肥地养鱼,塘泥可以肥林肥菜,菜叶果皮等垃圾又可以喂养禽畜。而在当前,这一完整的循环系统已经不复存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村禽畜饲养的减少和有机肥料的减少,这就使得化肥、农药、杀虫剂等用量不断增加,恶化了原本和谐的农业循环系统。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当前农村有机肥料已经退出农业生产过程。
有机肥料退出农业生产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有机肥的来源减少。传统农村有机肥有众多的来源渠道,如人畜粪便、秸秆还田、生活中的灶灰坑灰以及使用青草沤肥等。清代农学家杨岫在《知本提纲》中提出了“酿造粪壤”的10种来源,包括人粪、畜粪、草粪、火粪、泥粪(河塘淤泥)、骨粪、苗粪(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和皮毛粪等。而在当下农村,禽畜养殖减少、农民生活燃料改变,改变了有机肥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和循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民有更多外出打工的机会,农村社会每家每户养殖禽畜的习惯已经慢慢发生变迁,农民通过理性算计认为在家散养禽畜会浪费很多时间,更不如外出务工划算。如一个家庭要喂养一头猪,一天所需要的猪饲料3kg,花费6元钱,一个月的成本就要达到近200元钱。而且近年来养猪市场不稳定,猪肉价格时高时低也增加了养猪的风险。这样,农村养猪养鸡的人就越来越少,直接导致农家肥的减少。另外,传统时期农家肥的使用是一项体力活,不仅需要农民在养殖过程中经常向猪圈、羊圈中垫土以增加粪肥的厚度,而且需要身强力壮的农民将粪肥运到农田中去。当前50岁以下的劳动力基本都外出打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只有老人和妇女,即使有农户仍旧养殖禽畜,也很少有劳力能将粪肥运到农田中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已经不再使用秸秆、柴火等燃料,而大部分使用煤气、液化气等,这样以前可以肥田的灶灰坑灰和秸秆还田就不复存在。
其次,农民对有机肥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传统社会,有机肥是增加土壤肥力和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化肥、农药、除草剂和薄膜等技术的推广,农民开始放弃有机肥的使用。一方面是因为有机肥的制作和使用过程比较复杂,如要生产有机肥就必须养殖牲畜或者到山上割青草沤肥,人们不愿再从事这样又脏又累的劳动。而化肥的使用减少了很多麻烦,农民可以直接将其使用到农田中去。另一方面,农民现代卫生观念开始形成,大多数年轻人都形成了爱干净、讲卫生的思想,更不愿意接触粪肥等“脏”东西。这样,有机肥的使用就在农村丧失了其存在的主观基础,从而使得能量的循环利用成为不可能。而且,由于化肥的质量差或者过度使用都会造成土壤板结和污染,使得土地的循环功能丧失。据统计,到2010年我国每年生产的农药约200多种,加工剂500多种,原药生产40多万t,居世界第二。此外,长期以来我国化肥有效使用率仅为30%~40%,其余60%~70%都挥发到大气或淋溶流失到土壤和水域中去,对空气和土壤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广东广西等地区曾经存在生态循环利用的稻田养鱼系统,在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下也不断走向终结。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和“蔗基鱼塘”生态系统也由于有机肥等循环利用的减少而基本上被淘汰掉了。
再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减少了农民饲养牲畜的数量,也就减少了有机肥的使用。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村容整洁”的目标,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即要改善农村脏乱差的状况,因此政府出台了很多关于讲卫生、美化环境的政策。农民散养牲畜被认为不利于美化环境目标的达成,于是新农村没有人养家禽家畜了。而且,村民自身的环境观念也被改变,认为喂养牲畜会对农村社区的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在过去,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谁也不会说谁;而现在如果只有一户养猪就会将整个村庄弄得臭烘烘的”,村庄舆论压力的存在使得村民的环境观念不断被更新,从而从对热爱喂养牲畜转变为抵触饲养家禽家畜。“猪没了,狗多了”是现在许多新农村的新景观。
最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加速了有机循环的终结。随着农民外出打工机会的增多,打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大大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对生态的态度。对循环农业的直接影响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按照城市生活方式改造乡村,农民把打工挣回来的钱大部分用在建设和装修新房上,他们按照城市房屋的标准进行装修,安装完整的厨卫系统、下水道系统以及院落硬化等。以北京延庆县小浮坨村为例,目前该村已建设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和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大约有60%的农户安装了抽水马桶,农民生活污水和厕所都对接到下水道。这样,有机循环农业的直观感受就不存在了。对于一些住进楼房的村民,他们都不能回答“下水道的污水排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垃圾被送往了何处,这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二是对市场的依赖和大量过度包装、有毒物质进入了村庄,使垃圾变得异常复杂。
小浮坨村所在的村镇已经实现了垃圾的“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三级管理。每一户门前都摆放了3个垃圾桶,第一个是装不可回收但是可利用的垃圾,如灰土、菜叶、瓜果皮、厨房废物等等,村里收集后送到有机肥厂,经加工变成有机肥;第二个垃圾桶装可回收的垃圾,如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等;第三个桶装有害物,包括电池、荧光灯等。垃圾集中后由镇里统一送到有资质的垃圾处理厂处理。尽管如此,用该系统产生的“有机肥”并不被农民接受,原因在于进入这个系统的垃圾成分太复杂。按照城市的标准和观念,农村环境应该得到了改善,但这却导致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有机循环系统被破坏。农民生活中的生活垃圾以及粪便等本可以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返还到农田中从而实现物质循环利用,但现代生活系统与农业生产系统的分离,使得这种自然循环系统不复存在。在以上各种因素影响下,中国传统农业的循环观和循环实践都已经走向解体,并逐渐被以现代生产资料、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所取代。现代农业因为借助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工业产品,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减少了劳动力资源的投入,改变了传统农业单纯依赖人力、畜力和自然资源的现状。现代农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土壤质量下降、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特别是由于化学肥料的大量投入,使动植物副产品由宝贵资源变成了废弃物。现代农业技术应用走入误区,“以人的方法取代一切,无视大自然的力量,就连土壤的本质、肥料的性能都搞不清楚”[10]。这就使得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内部循环和双向循环变成了外部循环和单向流动,也就中断了农业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
现代循环农业的兴起和反思
现代循环农业是建立在以循环经济为基础、以“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reduce)、再利用原则(re-use)、再循环原则(recycle)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在当前农业资源稀缺和环境污染加大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依靠现代科技实现资源的低消耗、低污染和高利用的目标。从2004年开始,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发展循环农业的目标,“十二五”规划也提出了“以国家投入为引导,建立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在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农作物秸秆与畜禽粪便资源无害化处理、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清洁生产与产业链整合、农村社区净化等方面开展示范工程建设,以带动循环农业经济的广泛应用。鼓励农民使用沼气处理废弃物,对废物进行回收利用,鼓励农民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发展以产业化为基础的生态农业,以节省农业生产成本,改良土壤、改善环境卫生,塑造环境友好型社会,达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有机循环农业得到大力发展。根据循环农业发展动力的不同,可以对2种循环形式进行区分。一种形式是农民自发形成的循环农业模式。这种循环农业主要是农民自身意识到农业污染和农产品安全对其生活的危害,而主动采取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方式。如很多农民担心大棚蔬菜种植中的农药问题,于是就在自家院落或者田地中使用有机肥种植蔬菜供自己食用。随着有机理念的兴起,一些种植大户在自己的果园、菜地里也开始施用粪肥,一些蔬菜专业户甚至把“有机”作为品牌。有机肥的来源主要是农户从规模养殖场买来的,在小浮坨村,大棚种植户要从养殖场购买鸡粪,每车大约要花费200元左右,每亩地每年至少需要2车有机肥。
与传统循环农业相比,这种有机肥的使用方式并没有形成“有机肥—农作物—有机肥”的内部封闭式循环系统,而是借助外部资源形成的开放式循环,这种循环模式并不能实现资源之间的互补利用,而且存在潜在风险。第二种循环模式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如农村、城镇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生产有机肥和中水,但由于垃圾成份的复杂性,使得再次利用存在很大问题。这种循环模式具有极强的人工性,依赖污水处理、垃圾分离与处理等技术,注重高科技要素的投入,但却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规律和农业本身的特点和要求。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实施了“三起来”工程,其中一项就是“循环起来”,包括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污水粪便治理等。“循环起来”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但是在垃圾回收和有机循环利用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垃圾回收的本意是对分离的有机垃圾进行二次利用,但因为农村消费的城市化倾向使得农村生活垃圾具有与城市同样复杂的特点,农民很难严格按照分类标准进行区分处理。农户很容易将电池、药瓶、灯管、电子元件等有毒有害垃圾投放到可利用垃圾桶中,这样在二次利用中就会对农田、农作物造成不良影响。污水处理系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传统农户的生活污水成分是可知可控的,新农村污水的统一收集处理,其成分变得难以控制,这些含有有害物质的生活污水被循环利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对农业安全构成了危害。
因此,现代循环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利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等高新科学技术,更要借鉴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循环模式及其所蕴含的综合利用理念。具体说,在发展现代循环农业过程中我们应该树立2个理念。
第一,要树立综合利用的理念。传统农业虽然也把粮食的高产和优质作为重要目标,但粮食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目的。传统农业的产量概念和当今人们理解的产量也不尽相同,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把满足自身包括温饱在内的各种需要当作目标。因此,粮食作物的产量,不仅仅是粮食本身,而在于所有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各部分的总和。如要考虑人吃的、烧的、用的、住的,同时,还考虑家禽家畜的饲料、肥料等。这种生产观能使每一种生物都得到尊重和利用,这是传统农业保持能量循环、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的根源。为了种植多种农作物,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有意识地采取了多样化的生产方法和方式,这些多样化的生产措施不仅满足了农民自身消费的需求,而且对土地生产力的维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认为,现代循环农业要在借鉴传统循环农业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综合利用和发展的理念与策略,是针对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农业与农村发展方式,其核心是以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生产生活无害化为基本特征,通过“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生产方式,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二,要树立生态发展的理念。当今社会经过了“物本”时代,进入了“人本”时代,但是由于忽视环境和生态,财富增长了,生态却破坏了;个人的眼前利益满足了,但人类长远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生态的理念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建设新农村时,把安全的生态循环放在首位,在改变村民生活方式过程中,不是简单把城市生活方式作为目标移植到乡村,而是根据循环农业的特点,建立区别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循环途径。通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农业生产形态、农业组织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使之符合循环农业发展规律的要求。这是农业科学、生态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共同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本文作者:袁明宝、朱启臻、赵扬昕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