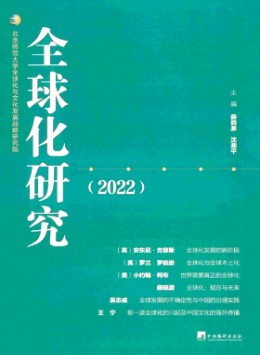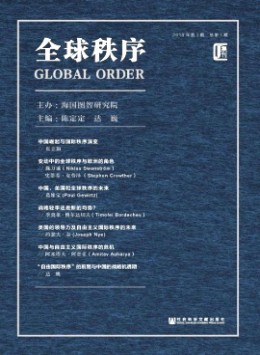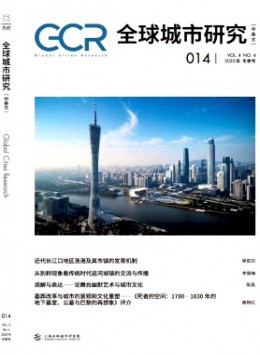全球戏剧城市形成要素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全球戏剧城市形成要素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伴随着从文本到舞台的形变,戏剧也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发生了空间变化,并服务于城市文化的转型升级。作为戏剧演出的场域空间,剧场成为城市“第三空间”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全球戏剧城市在戏剧内部演化和城市外部发展的动态平衡过程中应运而生。结合世界空间和时间的流变,依托戏剧特性及其与城市交互史的基础,我们认为全球戏剧城市的形成要素包括了“基因”“场域”“教育”和“气质”四个方面。
关键词:全球戏剧城市;基因;场域;教育;气质
一、全球戏剧的发展与城市历史的互动互融
城市之“蕴”映射于城市文化。戏剧作为多元文化艺术的组合,结合新媒体技术,突破其空间限制,与城市历史互动互融。宗教是戏剧发展与城市历史互动互融的起点。比如,公元前3200年的古代埃及,那时候的戏剧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宗教仪式。公元1000年之后,西欧国家的奇迹剧、圣史剧、道德剧在教会以及后来的演出市场上均获得了巨大的认可与反响。生活是戏剧发展与城市历史互动互融的基点。比如,反映市民生活和观点的宋杂剧标志着中国戏剧进入了成熟阶段。随后,明清传奇延续了宋元南戏的新兴变化,出现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第一次繁荣与第二次繁荣。地理是戏剧发展与城市历史互动互融的要点。比如,明代南曲系统的四大声腔是城市地理与戏剧融合的表现之一,包括了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其中,由昆山腔演化来的昆曲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政治是戏剧发展与城市历史互动互融的交点。比如,日本戏剧随着阶段、政权和城市的变化发生了许多更替。能言狂,含延年能、田乐能,从镰仓末期开始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戏剧样式,但随着德川幕府的灭亡和武士阶级的消失,其地位大不如从前。直到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举办了能乐源流表彰大会、昭和四十一年(1967年)建设了国立能乐堂等事件后,才逐渐趋向平稳。舞台是戏剧发展与城市历史互动互融的支点。比如,公元15、16世纪后,英国和法国的戏剧陆续搬上舞台演出,成为当前人们对于戏剧的第一印象。这也是全球戏剧开始国际传播的萌芽时期。如今,从纽约百老汇到伦敦西区,从阿维尼翁戏剧节到乌镇戏剧节,戏剧与城市的关系愈发密切,戏剧的全球化和城市的全球化正不约而同地成为一种趋势。
二、全球戏剧城市的空间共享与资源合作
戏剧,承载了经济转型与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多样性,[1]对于阐述城市空间共享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认为,全球戏剧城市,是指拥有完整的戏剧文化产业链以及多个成熟的戏剧文化产业集聚区,主要通过戏剧来推动文化创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创意经济提升的城市。据此,全球戏剧城市的代表有中国的上海与乌镇、日本的东京与利贺、英国的爱丁堡、法国的阿维尼翁、德国的柏林、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这些全球戏剧城市的所属类型依次为“经济与戏剧强强联手的城市群”“戏剧及其它文化均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以戏剧为主要文化与产业的城市”和“多重身份中戏剧属性仍较突出的城市”。全球戏剧城市的空间共享,主要包括剧作家创作的“文本空间”、演艺人员打造的“舞台空间”、观众参与体验的“剧场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以及融入城市建设的“景观空间”,都是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空间分化和利益群体分化的“戏剧类共享空间”。戏剧家何冀平在其戏剧作品的话语空间中承载了京、港两座城市的特点;《易卜生戏剧地理空间研究》一书解读了易卜生戏剧中“以南北方为框架的地理空间、以高山峡湾为主体的挪威地理空间、以挪威为中心的世界地理空间、以教堂塔楼为核心的宗教地理空间、以凉亭楼阁为主体的家园地理空间”的特点;[2]上海版《阿依达》的演出吸引了上百家媒体、三千多名演职员以及四万五千多名观众,创造了世界歌剧演出史上的多项吉尼斯纪录,在上海体育场实现了戏剧城市的“空间共享”。全球戏剧城市的资源合作,主要包括文化产业资源的合作、城市品牌资源的合作、戏剧人才资源的合作,从戏剧身份的视角推动了城市的文化艺术发展,深化了与城市其余身份属性的融合。例如,以上海和乌镇为代表的全球戏剧城市群,从经济与戏剧两个方面强强联手,为中国的戏剧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代的上海戏剧产业在当时上海租界的特殊空间环境中,形成了以戏院为市场主体的生产与营销机制以及从为产品找到合适的观众,到生产观众需要的产品的策略转变。[3]紧邻上海的乌镇在“古镇”“水乡”的标签中再增添了“戏剧”这一关键词,打造了国内首屈一指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文化品牌“乌镇戏剧节”,顺利完成了从“休闲小镇”向“文化小镇”的转变。[4]同时,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传媒学院等专业艺术高校也为这片土壤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工作者。
三、全球戏剧城市的形成要素
从全球戏剧城市形成的核心问题出发,基于但有别于全球城市应具备的“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三个关键因素[5]以及遵循在“能力支持、制度建设、规范引导”三重维度上参与全球治理[6]的要素,提炼出了全球戏剧城市形成的四个基本要素,分别是基因、场域、教育和气质。
(一)戏剧所在城市的“基因要素”一个城市的历史进程会裂变出相应的城市基因,正如张鸿雁提出用“城市文化因子”和“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来分析城市化与城市进化的关系那样,[7]城市的“基因要素”为进一步研究城市属性特色开启了新的切入点。城市滋养戏剧的发展,戏剧重构城市的基因。美国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的代表作《美国梦》以纽约为原型,通过揭露城市空间场域背后的故事,解读城市中的人物关系和社会问题,从而赋予城市真实形象。美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的作品则通过对时间的种族化和空间化处理,表现了美国黑人失去与非洲文化身份的联系后,开始寻找精神上的救赎与文化上的再联系,间接构建出了一部20世纪美国城市黑人生活史,[8]进一步阐述了只有对本族文化足够自信与自觉的民族,才能在精神上获得自我身份的救赎与被尊重。繁荣稳定时的城市基因与遭遇异族入侵时的城市基因截然不同,而这些不同的基因会无形地加入城市文化演变。例如,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后试图改造当地的歌仔戏,不仅遭到了当时歌仔戏艺人和戏剧工作者的抵抗,而且推动了中国大陆剧种与戏班大批赴台演出,折射出了中华文化根基的认同感与荣誉感。再比如经典戏剧《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具有当时英国的社会因素,但是经过改编的《哈姆雷特》(由尼克卢修斯、考索诺瓦斯和斯皮纳导演)则解读了东中欧戏剧潮流的发展,还清晰勾勒出了地区基因中的政治性和玄理二者在所谓“灵魂政治”的剧场中进行的交融。[9]
(二)戏剧生长空间的“场域要素”剧场,既是一个实体建筑物,又是一个透过演员和观众互动的观演场域,还是一个真实与虚构共存的创意世界。经过发展,剧场从单一观演机能转变为集剧场艺术展演、交流、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机能,包含了艺术创作与展示、观演体验与交流、艺术鉴赏与人才培养。位于伦敦南岸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和莎翁故乡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是兼具城市性和场域性的空间代表。剧场,作为城市文化场所,为城市提供了精神自由交流的空间。这里产生的艺术创造、思想交流和经济价值,是社会空间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城市亦给予剧场经营与管理的政策和资源,支撑戏剧文化的传承。有关剧场空间的设计与建筑,首要考虑因素是戏剧作品的呈现类型和观演需求。以日本平成初期(1989—1998年)为例,日本新建剧场至少有近20个,呈现出了日本社会对戏剧空间的巨大需求。以剧场规模来划分,有至少5个小剧场(小于500个客席数),至少5个中剧场(501至999个客席数),至少4个大剧场(1000至1999个客席数),以及至少3个超大剧场(大于2000个客席数)。如果说,布景城市和景观城市是常见的城市舞台形式,[10]那么,剧场是戏剧裂变及演化的内部空间,戏剧与城市发生的碰撞是戏剧发展的外部空间。以中国戏剧家曹禺为例,其戏剧创作的“场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大学和学院,另一个是剧团和剧院。前者包括了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国立剧专和中央戏剧学院,后者包括了中国旅行剧社、中央青年剧社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1]通常情况,外部空间的碰撞更容易成为人们现实生活接触戏剧的一个契机,比如,戏剧普及、剧作支援、戏剧节等。
(三)戏剧专业学习的“教育要素”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的场域。[12]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戏剧教育形成了创作性戏剧、教育戏剧和剧场教育等主要模式,适用于不同对象和需要。事实上,戏剧与教育,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戏剧教育是戏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戏剧人才的选拔、培养,关系到对戏剧史上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关系到戏剧艺术经验的总结、推广与提高。[14]比如,古希腊的公民教育中就有戏剧教育,中国古代的六艺中也包含着戏剧教育的元素。中国的现当代戏剧教育开始于20世纪初。第一所培养话剧人才的学校是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接下来是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南国艺术学院(上海)、高尔基戏剧学校(江西瑞金)、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要有职业训练和通识教育两种模式。“教育要素”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戏剧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部分,它的终极目标是人格教育,[15]像是综合性大学开展的戏剧美育,以及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戏剧普及教育,不仅能培养运用戏剧语言进行自我表达的能力,而且还丰富了教育手段。本文涉及的是狭义的戏剧教育,特指在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专业教育。例如,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上海的上海戏剧学院、香港的香港演艺学院、台北的台北艺术大学、纽约的茱莉亚学院、伦敦的皇家中央演讲与戏剧学院、首尔的韩国国立艺术大学等都是这些城市的戏剧高等教育阵地。
(四)戏剧文化传递的“气质要素”戏剧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又与生活保持距离,它传递的“气质”既深藏于灵魂、无形却有力,又根植于民间、平易且共生。纵观全球,18世纪启蒙时期的法国,戏剧作为商业与工业的兴盛图景,呈现出了“戏剧—节日”的最初构想,即戏剧的乌托邦起源,[16]那个时期的狄德罗和莱辛在法国和德国几乎同时创立了市民戏剧,为现实主义戏剧理念奠定了基础。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提倡的戏剧观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创作观念,推动了20世纪戏剧的理性转向。美国现代戏剧理论家、耶鲁大学戏剧系首任系主任乔治•皮尔斯•贝克先生于1905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了戏剧课程,又称“47工厂”,为美国现代戏剧培养了以尤金•奥尼尔为代表的戏剧中坚力量。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受到了中国京剧表演的启发,创立了“叙事剧”的戏剧理论。在国内,中国明代的屠隆以儒学为“嘉谷”、佛道为“甘浆”的三教合一思想在其三部戏剧创作《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中有着透彻的体现。[17]时任南开学校校长的张伯苓先生提倡新剧运动,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为宗旨,[18]进一步改善了当时学生团结力量薄弱、无组织能力的现状。[19]小剧场运动催生了中国现代话剧和现代戏剧教育,改变了中国新时期“戏剧危机”的困境,刺激了校园戏剧的新一轮繁荣。[20]这些人和事,都需要被置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全局中,在与传统规范、信仰、艺术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21]这也是戏剧文化连接当代年轻人的“气质”所在。
四、全球戏剧城市的未来思考
由于戏剧的艺术表现主要通过剧场空间内各要素的互动产生,因此,全球戏剧城市的评价指标应由总体戏剧实力、剧场空间和支撑条件三个维度构成,具体包括城市戏剧土壤、各类戏剧协会、各类戏剧教育机构、各类剧场空间、知名戏剧人、代表剧团、经典剧作、成熟的受众群体以及在智能化与个性化方面的创新等指标。未来,全球戏剧城市将遵循从“各自发展”到“相互竞争”到“联盟互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路径,形成四类联盟:一是国内全球戏剧城市联盟。以中国为例,联盟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乌镇、抚州;以英国为例,联盟城市主要包括伦敦、爱丁堡、斯特拉特福。二是区域全球戏剧城市联盟。以东亚为例,联盟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首尔、东京。三是洲内全球戏剧城市联盟。以欧洲为例,联盟城市主要包括伦敦、巴黎、柏林、罗马、雅典。四是洲际全球戏剧城市联盟。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戏剧城市群联盟。
作者:陈思 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