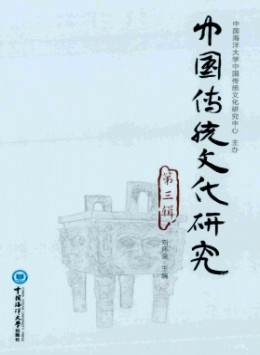袁静芳对传统音乐理论构建的贡献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袁静芳对传统音乐理论构建的贡献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袁静芳先生是中国传统音乐乃至我国音乐学研究领域的旗帜性学者。回顾袁静芳先生的研究轨迹不难发现,她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道教、佛教音乐研究,另一个是乐种学研究。本文通过对“乐种”与“乐种学”学术史的简短梳理及乐种学对中国音乐理论话语权建立意义的阐释等方面,论述从袁静芳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构建的贡献及意义。
关键词:袁静芳;乐种;乐种学;话语权;中国传统音乐理论
袁静芳先生是中国传统音乐乃至我国音乐学研究领域的旗帜性学者。她学养深厚、治学严谨、淡泊名利、为人谦和,其学术思想、成果及精神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及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回顾袁静芳先生的研究轨迹不难发现,她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道教、佛教音乐研究,另一个是乐种学研究。本文拟从袁静芳先生对乐种学的研究来管窥她对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构建的贡献及意义。
1“乐种”与“乐种学”追溯
“乐种”一词的来源,最早见于杨荫浏、曹安和合编的《苏南吹打曲》。随后,学者们对“乐种”一词的界定经过近30年的研究、推敲与雕琢,最终在袁静芳先生撰写的《乐种学构想》一文中确立了下来。随后,又经过11年的苦心研究与发展,袁静芳先生所著的《乐种学》在1999年出版,标志了“乐种学”的建立。从“乐种”一词的界定至“乐种学”的建立,虽然袁静芳先生功不可没,但也并非先生“一人之功”,她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多次提及对前人学者成果的观照与借鉴。例如:关于“乐种”的界定,她在《民族器乐》中说道:“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传统乐种的考察与研究,并参照其他学者历来对乐种界说的论述,1998年,在《乐种学构想》一文中,阐述了对乐种的界定。”关于“乐种学”的建立,她在《乐种学》中说道:“……并于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乐种学基础理论’课程,在过去前辈与众多学者对乐种的研究基础上,为乐种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开启了新的一页。”“收集整理(或译谱)乐种曲谱近百册,其中特别是前辈杨荫浏、曹安和先生对乐种所做的调查范例和研究成果,对乐种的实地考察、录音记谱、理论研究均具有开拓性、启迪性、指导性的楷模意义。”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观照,说明了袁静芳先生治学的严谨与规范,也印证了一个学科的建立所要走过的路,即学科称谓—学术成果—学科建立。虽然关于乐种一词界定的学术历史梳理,在袁静芳先生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多次提到且较为详实,但结合到乐种学的学术成果则较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学术称谓发展”与“学术成果发展”二者之间结合起来加以梳理,这样或许能使我们对乐种学的建立有更为清晰和直观的认识。根据年代及主要研究成果所显现出的研究特征,笔者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63年之前。1957年,在杨荫浏、曹安和合编的《苏南吹打曲》总论之七中,“乐种”一词首次出现。但仅是出现,两位前辈对乐种一词没有作任何界定与解释。其论述为:“在明末清初,约当十八世纪的时候,这种音乐,已与现在一样,一方面流行于民间,成为民间音乐的一个乐种。”此时,乐种的研究成果主要以两位前辈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如《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上海万叶书店出版,1952年)、《智化寺京音乐》(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油印本,1953年)等。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除理论研究外,主要显现出对第一手资料的挖掘、收集与整理,而对乐种一词的界定,学界几乎没有关注。第二时期:1964—1988年。乐种一词第一次有了界定,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其论述为:“不同的乐器组合,加上不同的曲目和演奏风格,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器乐乐种。”此时,乐种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高厚永的《民族器乐概论》、叶栋的《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袁静芳的《民族器乐》等等。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除了对乐种的音乐本体及文化特征研究外,更凸显对于研究对象的归纳与概括的关注。第三个时期:1988—1999年。1988年,袁静芳先生在《乐种学构想》中论述道:“历史传承于某一地域(或宫廷、寺院、道观)内的,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典型的音乐形态构架,规范化的序列表演程式,并以音乐(主要是器乐)为其表现主体的各种艺术形式,均可成为乐种。”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夏野、陈学娅的《中国民族音乐大系•民族器乐卷》,王耀华、刘春曙的《福建南音初探》,李民雄的《民族器乐概论》等等。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体现出对研究对象宏观归纳与微观个案研究的双重观照。许多关于乐种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袁静芳先生所提出的乐种界定的准确与科学。1999年,《乐种学》的出版标志着乐种学的建立,特别以袁静芳先生及学生们为主的研究群体陆续发表的学术成果,更是为乐种学的发展及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2话语权的建立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中西方音乐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愈来愈频繁,在频繁的交流中扩大了我们的眼界与认知,但也逐渐地暴露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关于“话语权”的问题在很多学者看来首屈一指。这里所说的“话语权”即用某种学术话语体系来解读某种音乐事象。例如用欧洲古典音乐理论体系解读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拉赫玛尼诺夫等作曲家的作品。然而,当我们试图用某种音乐学术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时候,似乎摆在我们面前能选择的话语体系很少,除非借用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但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用欧洲音乐理论体系来解读中国音乐的时候,很多状况下我们是失语状态的,即因所言非所达,而出现的失语或言无意的情况。例如,如果套用西方古典音乐曲式分析理论对山西八大套中《箴言》套的曲体结构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必然是有失偏颇的,甚至会产生“老虎吃天,无处下爪”的情况,从而在与他人言说(交流)时,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追其原因,除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用西方的理论知识体系生搬硬套用于中国音乐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事象不成正比。换句话说,中国传统音乐的品种、内涵等非常丰富,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却显得滞后,形成研究理论与研究对象不对称的情况。相比西方,他们不但有着辉煌灿烂的音乐文化,而且音乐理论体系也非常完备、科学。比如曲式分析学,西方音乐曲式结构理论有着极为严密、科学的体系,几乎可以作用于任何一部西方音乐作品,对其内部结构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与解读。然而中国传统音乐的曲式结构分析,从目前来看仍处于发展阶段,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时我们不得不借用西方曲式结构理论来作阐述。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如客观历史、音乐教育、学科理论建设等等,正如项阳所言:“与西方音乐教材早已体系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体系尚未经过系统梳理,音乐院校的教师们因应教学需要对传统音乐形态不断探索、不断架构并充实到教学和教材中。”由此不难看出,我们亟需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不断丰富、提出、提炼、检验我们自己的理论。袁静芳先生的乐种学理论,无疑给我们建立话语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袁静芳先生的乐种学理论分别从“乐种的物质构成”“乐种的形态特征”“乐种的考察步骤与方法”“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乐种的体系”“乐种与社会文化”等关于乐种研究的六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特别是对“乐谱”“旋律发展手法”“宫调”“曲式结构”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对于我们建立中国音乐话语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应用这套理论,完全可以对诸多中国音乐事象进行解读,从而完成用中国音乐理论体系解读中国音乐的话语叙述。而“乐种的考察步骤与方法”“乐种研究中的模式分析法”“乐种的体系”更是建立了一种研究范式,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学者来说这是“授之以渔”。很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完全可以应用这些理论直接进行作业,对于今后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及话语建设有着重大意义。我国有着丰富的乐种文化遗产,对它们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研究,使研究成果能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每位学者都必须谨慎思考的问题。而乐种学的建立,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
3乐种学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自身的教育发展,学科教育发展的规范化,也会促进学科自身长足的发展;反之,这门学科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从学科属性上较难理出乐种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学理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即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特性,是不言而喻的。就从目前各大艺术院校所设置的专业与研究方向来看,还没有一所院校设置专门的“乐种学”研究方向,但在设置中国传统音乐专业的院校中,很多学生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乐种学,甚至有些研究就是对乐种学的研究。从目前学术界较为公认的中国传统音乐四大分类、民间音乐五大分类中,与乐种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民间器乐,但是乐种学也涉及到了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及文人音乐。不过,当下的传统音乐教学,特别是本科层面受到学时、学制等客观原因限制,很少会有讲授到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及文人音乐,很多院校仅能勉强讲授完民族民间音乐。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生教学层面来看,很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是某一乐班、某一具体乐种研究。如果我们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进行对比的话,不难发现其乐种学教学是个“断档处”。本科生在本科阶段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乐种学训练,到了研究生阶段却要灵活运用乐种学的相关知识。那么,弥补这个“断档处”的正是袁静芳先生的乐种学。虽然乐种学并不是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独立学科,但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学生们在撰写学位论文,学习了解相关知识的一个“武器库”。褚历的《内涵深厚、桃李芬芳》一文中提到:袁静芳先生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就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而言,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是收集整理资料并进行分学科的研究与著述;20世纪后期,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为对某些分支学科微观研究的深入,新的学科不断建立,如乐律学、乐谱学、乐种学等。而21世纪研究发展的总趋势是研究中的综合性、交叉性、系统性。由此不难看出,袁静芳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是站在学科统筹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的,并对后学们寄予厚望,也给后学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了能使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向前发展,从而服务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袁静芳先生及她所创的乐种学,无疑是为后学们在学习与研究中提供了一把金灿灿的钥匙。乐种学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贡献,将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越来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4结语
中国传统音乐历经千年,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是某一人、某一时所能了解、所能悟透的,它几乎伴随着整个中国的文明史。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传统音乐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近年来,又受到教育制度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音乐教育制度的影响,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知出现了些许偏差。学界始终关注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但与西方音乐研究体系相比,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在方法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着明显欠缺,致使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至今仍要使用西方术语。建立健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体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袁静芳先生的乐种学,无疑是个很好的开端。对袁静芳先生乐种学的研究将使我们可以在前辈们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对学科建设起到积极作用。笔者有幸,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曾跟随袁静芳先生在2013—2014年完整地学习过一学年的《乐种学》课程,并在袁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结业论文《对山西笙管乐套曲〈箴言〉的音乐分析》。那是一段非常充实的时光,每周上课前,袁先生总会带给我们一摞资料让我们学习。在每节近3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袁老师尽心尽力地讲授,让笔者很难相信她是一位已年至耋耄的老人。她治学的严谨、思维的开阔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将使本人受用终生。
参考文献:
[1]杨荫浏,曹安和.苏南吹打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7.
[2]袁静芳.乐种学构想[J].音乐研究,1988(4):16-23.
[3]袁静芳.乐种学[M].北京:华乐出版社,1999.
[4]袁静芳.民族器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高厚永.民族器乐概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6]叶栋.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7]夏野,陈学娅.中国民族音乐大系:民族器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8]王耀华,刘春曙.福建南音初探[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9]李民雄.民族器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
[10]项阳.构建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与教学实践之路[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3):33-41.
作者:潘捷 单位: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