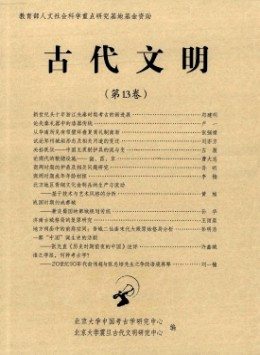古代音乐艺术及美学思想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古代音乐艺术及美学思想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强调音乐艺术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宗法礼教的社会则强调“乐”必须为“礼”服务,最终必须为政治服务。音乐美的形式,不在音乐本身,而在于它是否对政治伦理有作用,也就是说是否达到了“善”的要求。美和善是评价中国古代音乐从内容到形式是否统一的最高标准。孔子极力反对郑声,那是因为“郑声淫”虽美但不善。当他听了《韶》乐后,评价此乐曲不但“尽美”而且“尽善”。而听了《武》乐,则认为虽“尽美矣,未尽善也”。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的音乐思想,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音乐有着极大的政治作用。虽然孔子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但他对音乐的主张,对后来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一直影响着中国音乐数千年来的发展。这一时期有关音乐美学的理论,还有道、墨诸家,他们对于“礼乐”的问题,存在不同观点,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争论的焦点即音乐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墨家对音乐采取否定态度,法家吸取了情感说的合理性,提出了音乐形式美的“善音”说,批判了墨家的“非乐”倾向———法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人民性,直到今天也不失参考价值。道家采取躲避现实的态度,对音乐像他们对待所有事物一样,把人们对音乐的要求视为“欲”。老子说:“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又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1],是彻底的非乐观点。上述音乐思想的争论,不在于音乐艺术要不要从政治伦理中独立出来,而是能不能紧密地和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最终统一在“乐与政道”之下。儒家在长期的论战中发展巩固了这一思想,把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发扬光大的是孔子的弟子公孙尼子的《乐记》,它继承和发展了前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提出“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2]的理论。同时认为“乐”的目的,就是“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3]的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继《乐记》后,汉初儒生毛苌的《诗大序》进一步使这一学说得以发挥,提出诗歌与艺术的目的,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儒家之所以反对“郑卫之音”只因它是“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也”,它所引起的是“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和而不可止也”,是完全不符合宗法社会政治伦理要求的。中国音乐从周朝开始便被儒家划分成雅乐与俗乐,雅乐是代表朝廷的正统音乐,俗乐则为民间音乐,被认为是“繁手淫声”而一直遭贬抑。中国音乐就一直在雅与俗的对立与“斗争”中发展与传播下来。《乐记》曰“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行政其极一也”[2],所以“同民心而治道也”。统治者还专门设有采风官、采诗官,“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样的“言志、咏声、动容”就变成了不仅仅表现主观感情的问题,还带着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这一“言志咏声动容“论,一直到魏晋时代才受到了冲击,转变为缘情说。马克思在论述中国革命时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4](P545)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更换并不能使中国音乐产生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是与新的政治伦理结合在一起,为新的统治阶级服务,增加和补充更加具体的“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新内容,更加强调音乐对人们的教化功能,严重地压制了音乐的娱乐功能、重内容轻形式,强调礼乐结合,把音乐当成政治工具,这在产生它的时代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对以后逐渐产生消极乃至某种反动作用。封建宗法的这一思想体系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音乐的美学思想。
二、中国古代音乐的等级色彩
西方国家中世纪依靠宗教,近代和现代依靠法律;中国传统社会依靠的是名教教化。名教的核心是等级差别,这一差别代表地位的差异。礼乐本身,就是这种差别的表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5]君臣、父子、夫妻,上下不同等级的人,行不同的礼,享受不同的待遇。而这一切又是取法天地而立的。以乐舞来说,古代舞队的排列为佾,舞佾的排列按职务高低有严格的规定。天子六十四,诸侯三十六,大夫、士一十六。鲁国的陪臣季氏,因为用了天子舞佾的排列人数,孔子十分气愤,说:“季氏八佾舞于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6]又如对五声音阶本身的排列也有严格的规定,五音分别与君臣民事物联系起来,认为“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2],五音有尊卑,不能相叠置,或相混、超越,如果违反了次序就会造成混乱。这种违反音乐本身规律的做法,大大地限制了人们的音乐创作,扼杀了人们的主体创造精神,使民族的精神本体、性格受到封建伦理的规范与钳制。民族精神本质、性格心理虽有很强的内在创新活力,但更多的是凝滞与保守。精神方面如此,物质方面更是如此,如住宅的式样、规模,交通工具,服装款式等,无不遵照等级规定严格执行,不能越规,否则就会遭到“不仁也”、“非礼也”、“无君也”、“无父也”的指责。在这种等级观念的支配下,一方面人们受到层层限制、约束,另一方面讲究身份、气派、威严,炫耀富贵成为宗法社会的审美观念。孔子本人虽不富,却也很讲究“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历代封建帝王和统治阶级更是如此。《韩非子•内储说》记载,齐国的统治者宣王每次听乐,必须有三百人为他吹竽,以至于有滥竽充数的人混在乐队里很长时间都没有被发现。他并非是真懂音乐,而只是为了讲究场面的宏大,气势壮观。在封建社会,统治者认为场面的讲究就是美。因此他们炫耀自己的财富,互相攀比,挥金如土。他们不惜财力做大钟那样的贵重乐器,以乐队舞伎作为礼物互相赠送;有时一国的最高统治者也用乐队与乐器作为奖品,赐给手下的贵族。历代统治者所要达到的美学效果,就是政治上的神圣感、庄严感。在以富为美的思想指导下,各地诸侯、卿大夫纷纷大兴土木,讲究场面,这对百姓来说更加重了压迫和剥削。评论者常把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失败,甚至亡国的结局,和他们对音乐的爱好联系起来。虽然过于片面,但也包含着一部分真理。
三、中国古代音乐的“和”的色彩
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美在于和谐。他们发现,“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的比例所组成的”[7](P32-33),还提出了有名的“黄金分割”。可见他们是在对客观事物的分析研究当中寻找和谐,寻找美的原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讲“和”,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和谐;而这种和谐,强调的是人伦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和”的原则。他们讲的“乐”不仅是音调按一定数量比例而成的组合,还是“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比;序,故群物皆别”[8],“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宫矣”[5]。乐与礼本是天造地设之物,不是人们根据什么原则制作的;只有通天接地的圣人才可以“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音乐的和谐不是得自人工的音调排列,而是宇宙运动的结果。和谐与人伦、自然一开始就是三位一体的。音乐艺术的作用,就是要在等级森严的秩序中创造这种“和”的气氛,达到一切事物都能融洽共处。《乐记》是我国最早的美学专著,它的音乐美学思想从头到尾,都贯穿了一个“和”字。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5],就是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和”,从个人到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是贯通一体的。在这种美学思想直接影响下,中国古代音乐在结构、旋律、音阶、节奏、节拍等方面,大多强调统一而缩小差异,如“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9],“凡乐,天地之和”[2]。荀子的《劝学》篇中有“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这种追求和谐、和顺、和美、和敬、和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和”的美学思想,正是我国内向型、静态性社会心理与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追求温柔敦和的阴柔美、空灵美便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的重要风格之一。道家有别于儒家,道家强调“乐”是主客体超功利的无为关系,是内在精神,并非认识性规律。在音乐上形成以玄想为重,以诗意为归,注重神、韵、味的抒发的审美观。这种审美心理在中国古代音乐中的代表是古琴音乐。古琴曲清、静、淡、远、和、古、澹、恬、逸、雅、丽、亮等“二十四况”,是受启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而提出的古琴乐审美范畴。“和”这一审美观在古琴音乐中具有多义的内涵,同它汲取儒家之“和”的多种观念有关,如“和”在古琴理论与实践的目的在于陶冶人之性情并使之归于“和”的认识,就同儒家学派“乐之务,在于和心”[10],“乐者,审一以定合”[11]的认识相一致,并具有社会伦理学的意义。“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5],肯定了“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只要人在“礼”的制约下“自戒惧”,“自慎独”,就既可以达到个人内心的平和,亦可达到天地之和,天人之和,情景之和,它们是可以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乐”就是要把个人的“和”而贯通到天地的“和”。儒家把整个社会、国家看做一个宗法群体,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这个群体的派生物,个人的“和”要服从群体的“和”,达到天地之和,最终必须遵遁“礼”所规定的行为准则。而西方则强调“个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专注于个性的发展,“要表现自己并且要在表现中找到快乐”[12]。以人为本位,向外开拓、征服,它是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同时获得支配自然的权力,从而达到自由的王国。与中国古代思想的群体原则强调和谐、对称、义务、尽性尽命、大一统不同,西方的个性原则更多强调自由、本位、权利、多样化。可见,中西方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人生观,中国的观念是要达到一种“天人感应”、“物我交融”,最终达到万象森然的气象和境界;西方从物质利益原则出发,导出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正因为如此,西方的美学思想强调艺术反映斗争,写反抗,写人对物质世界所起的作用。贝多芬对《c小调第五交响乐》(命运)乐曲开头的四个音符作过这样的解释:“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因而后人称这部交响乐为《命运》交响乐,这部闻名世界的交响乐表达了作者所坚信的“通过斗争获得胜利”的光辉思想。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大胆讽刺和反抗农奴制度复辟,歌颂了法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胜利。由于该剧的政治倾向性十分鲜明,被法国统治者一再下令禁演长达六年,经过人民不断斗争,1784年才在巴黎首次演出。这种精神在中国古代“中和”的音乐思想中,是难以找到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如杜甫、范仲淹、关汉卿、岳飞、苏武、屈原,他们都可以“怨”,但不能“怒”;可以对宗法社会“刺”,但不能“乱”了专制统治。《乐记》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义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也就是说,音乐艺术所表现的情,要合乎宗法社会的“礼”,这就是中国古代音乐“和”的美学思想的精髓所在。
四、中国古代音乐的“感情”色彩
中国古代艺术重视对对象的直接感受,在感受中触发联想与感悟,然后情动于中,形于生,声成文,方为乐。“夫乐者,乐也,人情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13]这是把感情放到了音乐艺术的首位。此后《礼记•乐论》又发挥了这一思想,强调:“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这就进一步把音乐的起源和本质,归结于“人心感于物”的感情和审美意识。中国古代音乐艺术往往在直接感受中追求个人精神境界与外部世界的暗合,即把个人情感外化于自然。二者有内外之分,但实质上是一致的。个人感情与社会目的的统一,“礼”与“乐”的统一,是宗法礼教美学思想的理想要求。我国古代对艺术表现感情的说法和要求,明显有异于西方的民族特点。西方音乐艺术从浪漫主义阶段开始,音乐家们就纷纷以个人情感为基础,构筑个人主义的精神世界。他们冲破古典主义艺术的束缚,为西方文化的艺术园地增添了不少光彩。西方艺术中有大量谈论“感情”的论著,他们热衷于从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论述感情,因此他们重快感,重视情欲,甚至把感情当成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弗洛伊德学说的思潮曾影响到几乎整个西方的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的文学艺术领域,乃至一代人的人生观。我国古代,虽不完全否定这种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但却不承认这种感情是宫廷音乐家所要表现的。中国古代长期把音乐划分为雅乐与俗乐,儒家“扬雅绝俗”的主张也一直影响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因此只有帝王的国乐,无民间的民乐,琴瑟的中正平和之音,也不是一般民众所能听懂的。《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又说:“先王之制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还有:“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以上记载都是说人的感情固然重要,但不能为物欲的满足有过分的感情欲望,应当不断地加以节制,否则人们就会无所不为。儒家所倡导的许多礼乐制度,一开始就是从人的感情的自然需要出发的:“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止,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2]这里把祭祀的悲伤感情,干戚歌舞的热烈感情,婚姻的喜悦感情,射箭、宴会等社交活动的欢乐气氛,都描绘得十分生动,充满了感情色彩,但这些感情的抒发都应适度和有所节制,礼、乐、刑、政各自发挥其社会作用,而且相互没有抵触,都是为了政治伦理的需求。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是以“礼乐”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它之所以能有如此久远的生命力,除了政治伦理之外,还在于它重视人的感情。然而儒家“重情”说也有着欺骗性,他们是本着人的感情需要来谈礼,来谈乐;历代帝王利用这一礼乐思想对人民感情的自然需要进行扼杀。于是,一些欺骗和麻痹人们思想情感的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作品,也就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音乐美学思想,大多重视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感情,无视人民大众的感情。封建帝王“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11]就是佐证,其结果则给人民在感情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礼乐”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干,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封建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综上所述,从中国古代音乐论著中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特点,大致有上述四个方面,其他都可以从上述诸方面引伸出来。中国古代音乐的形成及其优劣的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里只是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特点上谈点粗浅的看法,求教于专家学者。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