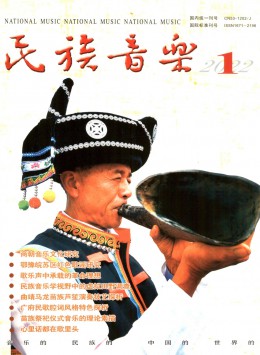音乐表演的真实性探讨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音乐表演的真实性探讨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近年来的学术实践也表明,音乐表演首先是一种体验性的艺术,实证性研究在认识论层面的价值固然令人信服,但其最终无法全面涵盖表演艺术直接触及人类情感体验的实质机制,因此,从音乐表演艺术本体论角度深入把握其可知可感的内在规律,是这一学术领域继续掘进的必然要求。
国际音乐表演理论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体现出“传统的历史研究逐渐与分析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结合,越来越体现出多样化的跨学科性质”②。尤其是非西方音乐表演理论研究的介入,使这一学科的研究视域逐步跳出欧洲经典音乐理论的框架,非西方音乐表演艺术的“作品”及其体验特质,不仅充实了传统表演艺术理论的分析素材,而且在理论视角上也进一步饱满化,于是,针对音乐表演实践的艺术真实性问题,率先成为这一领域的理论焦点。其具体表述是“相对于‘作品’,如何表演才算是真实”。按照彼得•基维的说法,所谓音乐表演的“真实性”包含四层含义:一是忠实于作曲家的表演意图;二是忠实于作曲家生活时代的表演实践;三是忠实于作曲家生活时代的表演音响;四是忠实于表演者个人原创性的而非仿效的表演方式。③基维的提法,突破了19世纪古乐复兴运动所设想的围绕作品展开的音乐存在观念,将其延伸为作品、作曲家及其所处时代的表演结构。
可以看到,国内外音乐表演理论,其出发点不同,但都有整合实证分析与主观阐释理路的趋势。如何“合理”、“正确”地演奏一支弦乐四重奏,才能符合作曲家海顿的创作意图,重现18世纪的表演技巧和音色?这已经不是一则表演者必须照搬的铁律。在特定时空中创作产生、流传的音乐,并不一定需要把在特定情形下设计出来的力度、速度、音色、语气固化下来,作为绝对精准的模本去重现;更不用说,附着于音乐背—后的表演氛围、听众期待、表演价值等历史存在物,更是难以捕捉并固化的。约翰•凯奇的《4'33″》要求钢琴家在一定时间内静坐在钢琴面前做“无声”的表演,每一场的观众听到的是不同的现场声音:呼吸声、观众席的骚动声、演奏厅中轻微的回响等等,这时候,何谓表演文本、表演符号、表演声音,乃至表演的作品?如何重现这一作品的“原貌”?这些问题顿时会导致一种理论上的虚无,也可以说,颠覆了以往文本意义上的重构作品真实性/原貌的思维动力。凯奇采用的是一种极端的做法,但他对浪漫主义时期以来围绕西方音乐作品形成的“本真表演”的实证传统提出了反思。此外,作为一种表演体裁,爵士乐的表演,也对传统意义上的“本真表演”和“作品”提出了挑战:当每一次表演时,音乐素材的呈现主要来自乐手们当下的音乐感受和表达习惯时,固化的文本和实践概念再次被消解或重构。
与西方古典(实际意指“经典”)时期以来对表演文本、实践和真实性重构的历史认识相对照,中国语境中的音乐表演,更早表现出这种独立的历史存在。对历史时期曾经存在过或流传下来的中国音乐如何看待?如何付诸实践?如何评价其实践?传统中国音乐家或者历史典籍,对这一问题基本上采取了稳定连贯的态度。即所谓“五帝殊时,不相沿乐”。数千年来形成的针对古乐的表演传统,连圣君治下的贵族音乐都要求有不断更新的解读,何况是主要以娱乐形式存在的民间世俗音乐?所以说,20世纪以前的中国音乐表演对象,“变动性”是其主流性格,定谱、定腔、定声只不过是一种时间片段存在,一旦表演功能、场合、表演者有所变化,表演文本就会合法地流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20世纪以前的音乐表演传统,恰恰为西方自1800年以来确立起来的与表演有关的观念和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对象,也成为西方音乐表演理论开始反躬自省的思想资源之一。
这样的学科进路可以有多种选择,也可能会出现具体理论描述与实践上的复杂冲突。一首作于18世纪的康塔塔,能否仅仅参照艺术观念、复古乐器、声音想象等因素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得到合理的重构?或者反过来假设,一首明代民间小曲是可以根据上述相同的因素复现于西方音乐厅?这样结果的“真实性”显然令人置疑。也就是说,产生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艺术“作品”中的异质性因素不是那么能够轻易重构的,其最关键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上述表演诸因素的组合,而是如何把握人类音乐体验的超时空性。准乎此,则18世纪和21世纪的东西方音乐听众,是有可能在类似的作品或表演实践过程中获取相近的音乐体验的。
于是,海顿的交响乐,凯奇的先锋音乐实验,巴赫的康塔塔,明清无名氏的小曲,经过上述因素的细致考证分析,给以跨时空艺术观念的反复探究、协调,会产生对当代人真实而有意义的艺术体验。所以,文献的、思想的、乐谱符号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分析与阐释,正是当代中西方音乐家或音乐学者需要以历史的、整体的眼光加以审视辨析的。在此,历史的视野和情感方式构成了这种当代重构活动的拓展维度。因为所有经过历史沉积下来的音乐作品/活动,不止表达了当时人的主观体验与时代风格,而且也指向了未来。这正是上述重构方式的美学原因。现在看来,以往表演语境中所谓“忠实原作”背后的推动力,正是表演美学上的“客观性”思维,①通过追寻音乐表演的“客观性”去接近历史作品的“真实性”,显然过于单薄,失去了主观体验的维度,也就等于放弃了历史表演最本质的目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历史上的音乐表演,还是当代试图要重现的历史音乐作品,本身不存在绝对的实体,“即便是汉斯利克所声称的‘音乐中的唯一存在’———亦即‘乐音运动’,也只是心理学上谓之‘似动错觉’的现象而已:须知一个音是不可能‘进行’到另一个音的”②。由此可见,如果说音乐表演在器物和观念层面可以是历史的、时空属性的,那么人类的音乐体验则完全可以是超历史、超时空的。这正是当代音乐家表演历史时期音乐作品或从事历史性质的音乐实践活动时,所宜采取的学术姿态与方式。
对音乐表演真实性问题的这些认识,不只是学术性研究或严肃表演中需要认真思考,今天在当代艺术表演出现的某些混乱和矛盾的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正是对上述问题缺乏反思所致。本文所探讨的音乐表演的真实性问题,涵盖了严肃表演和大众表演的宏阔范畴,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表演形式的问题,而实质上却又与音乐作品的历史存在、真实性、当代趣味等美学问题息息相关。鉴于此,当下的音乐表演理论研究,很有必要在这个路向上深入掘进。(本文作者:童师柳 单位:绍兴文理学院音乐学院)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