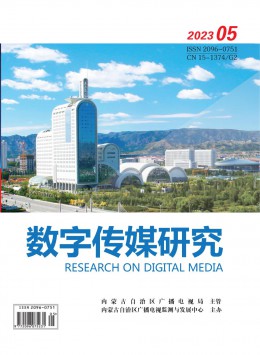数字时代艺术创作主体重构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数字时代艺术创作主体重构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一、创作主体的沦陷
网络与以往的媒介相比,是一个交互性和多元性的媒介,具有马可•波斯特所说的“双向去中心交流”的特征。“双向”是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无重点、无指向的相互交流,“去中心”是指信息传播的非中心化繁殖,信息中心的无意义。也有学者认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艺术原有的创作、传播、接受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三者不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言以蔽之,即艺术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创者、传者、受者的‘三位一体’化。”[4]数字化的参与模糊了接受者和创作者的界限,也使传播者的权利大大缩水,原有的至高无上的创作者主体地位已经沦陷。
(一)机器的喧宾夺主
机器的喧宾夺主有三种情形,包括智能体、交互体和机器作者。
1.智能体库兹韦尔认为:“所谓智能就是能够最优化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去实行上述目的。对智能还有许多其他的定义。其中我最欣赏的是R.W.杨的说法,‘智能就是在一件原本认为杂乱无章的事情中发现规律的能力’。”[5]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1940年,诺伯特•维纳提出有必要来研究一下人类和计算机直接的关系。1948年他写出《控制论———动物与机器的控制与传播》一书,将控制论视为信息理论的一部分,关注人、机器和动物中的通信问题,界定了控制论的三个重要观念,即交流、控制和反馈。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的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阿兰•图灵在1950年时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计算机和智能》的论文,提出了“机器能够思维吗”的问题,在答案是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测试标准,来判断电脑是否像人那样思考。这个测试后来被称为“图灵测试”,这对后来计算机以及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1956年夏季,以麦卡赛、明斯基和申农等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在一起聚会时,共同研究和探讨用机器模拟智能的一系列有关问题,并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这也标志着“人工智能”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诞生。渥维克认为:“人工智能不是对计算机进行研究,而是对思维和行为所体现的智能进行研究。计算机通常是智能的工具,因为智能理论一般通过计算机程序表达出来,是计算机能够做那些人类需要使用智能去做的事情。”1997年,IBM公司“深蓝”(DeepBlue)电脑击败了人类的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巴罗夫便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完美表现。2012年6月底,在英国著名的布莱切利庄园中举行了一场国际人工智能机器测试竞赛,由俄罗斯专家设计的“叶甫根尼”电脑程序脱颖而出,其29.2%的回答均成功“骗过”了测试人,取得了仅差0.8%便可通过图灵测试的最终成绩,使其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接近人工智能的机器。对于机器智能体与人的关系,很多视听艺术作品都有涉及,尤其是在电影中,比如《终结者》系列、《黑客帝国》系列等,都表达了人类对于机器智能体的向往、猜测,甚至是害怕。写出过基地系列和机器人系列的科幻小说家伊萨克•阿西莫夫认为,机器人是可以根据程序为人类服务的。早在1940年,他和约翰•坎贝尔(JohnCampbell)就提出过机器人定律,后来又经阿西莫夫的发展而定型,这些定律植入到他的机器人电路———大脑里。
2.交互体除了智能体的功能,机器还是一个交互体,和人类的交互可更加强大机器的功能。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一书中曾预言人们在网络中与电子器官连接的情形:“我们都将成为变形金刚一样的电子人,可以随时随地改头换面———根据需要的不同,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租用外在的神经纤维和器官,并重新调配我们的空间延伸部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师曼恩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将相关的机器设备与自我交互起来。他相继发明了可穿戴电脑供摄影之用,为可穿戴电脑加上了生物传感器,以及可穿戴摄像机。1997年,他在多伦多大学建立了电子人社区,有20多名用可穿戴电脑或者可穿戴计算机装备起来的成员进行彼此的无线通信。2013年10月,美国电视台播出纪录片《不可思议的生化电子人》,主要讲述工程师们如何利用人造肾脏、血液系统、植入电子耳、电子眼等组件,组装成能实际操作的机器人。而一批美国工程师制作出的逼真生化电子人已经亮相于同年10月的纽约国际动漫展。2013年8月24日傍晚,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6岁男童小斌斌被骗至野外,被凶徒挖去眼球导致双目失明,据香港《明报》网站报道,香港眼科专家林顺潮表示,一队医疗专家已抵达山西探望小斌斌。小斌斌失去眼球,右边眼腔骨破裂,而他的视力系统已发育,有机会通过植入电子眼恢复视力。电子眼是把失明人士的视网膜连接上一双获取实时图像的眼球和一个微小的由激光发动的集成电路,主语重复利用放在眼内的小型数码相机获取实时图像,把影像送到接在视网膜背后的集成电路片中,电路片的电极会形成一个图像,图像刺激视网膜,使盲人可以“看见”。电子眼的最大妙处在于它可以与电脑连接起来,实现人脑与电脑的真正结合,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也有作者对于人机交互提出反对意见,德克霍夫认为,“我们纳入生活中的每种技术延伸都能起到一种幻肢的作用,但它绝不会被真正地整合到我们的身体或者心智功能中,也决不会真正地脱离我们的精神气质”,并由此建议“大多数电子技术都不会使身体遭到遗弃,而会重新筹划我们感官的活动方式,从而使我们能够适应个人心智与集体心智的一种组合”。
3.机器作者离开与人的交互,机器本身也可以成为实践活动的发起者,机器已经可以喧宾夺主,单独成为作者,被称为“机器作者”。机器作者历史悠久,早在1805年JaquetDroz公司分部主管、瑞士机械师梅拉德特就制作了一部自动写作机器,以发条驱动,可以绘画、写诗。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个人电脑及其辅助智能的运用就受到了科幻小说家的青睐,多部小说的内容涉及机器的智能功能或者创造功能。20世纪中后期,最为知名的大概要数米翰开发的交互性程序“故事编织”(Tale-Spin,1977),这一程序的基础来源于他的博士论文《元小说:用计算机写故事》,这是用Lisp语言写成的。1990年,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特纳发表《吟游诗人:一种叙事与创造性模式》一文,其所开发的程序“吟游诗人”,需要10000行代码才能生产出一打不同的有关亚瑟王的故事情节,“它以小量的知识开始,能够通过有力的逻辑与类比的推理将这一数据扩展为故事”。2000年,美国学者布林斯约德和费鲁齐开发的Brutus是一个故事生产的架构,由知识和处理两部分组成,知识部分包括各类所需的知识,处理可将知识生成故事。关于计算机和艺术家关系的探讨也由来已久。渥维克说过这样一种情况:“由于人脑和机器脑不同,机器将呈现与人类形式不同的情感、自我意愿、意识等。或许如果我们使用生物学技术,努力使机器尽可能接近人脑,那么很可能机器的特征将变得近似于人类特征。”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米切尔曾在《在终端的恐怖:某些艺术家如何看待计算机》(1999)一文中分析了某些艺术家害怕计算机的原因,其中包括担心计算机将代替人、计算机不配作为艺术工具等。她认为,“计算机能够生成包括不规则形状在内的各种模式,比人类所能做的更为迅速、有效,由此而出现的模式是不同寻常、优美的———一种没有艺术家的艺术”。但她依旧认为计算机不具备作为艺术基石的创造能力,所以计算机不能取代艺术家。可以说机器作者的创造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计算机诗人已经出现,网络流传着大量计算机诗人创作的诗。2008年1月,第一部由电脑创作的小说《真正的爱情》诞生于俄罗斯。此书以《安娜•卡列尼娜》主人公的经历为情节主线,时空出现大挪移:沙皇时代的红尘男女一脚迈入21世纪,荒无人烟的岛屿替代了繁华的圣彼得堡……电脑小说的面世首先是圣彼得堡的程序专家在语言学家的配合下,推出了名为“PCWriter2008”的小说创作程序。语言学家和电脑专家共同为每个主人公建了一份详尽的档案,包括外貌、语言习惯、心理特征、性格特点等。程序借助这些资料能够衍生出各个人物对外界不同刺激的反应,甚至作品的修辞风格也是事先设定好的。最后,电脑发挥的是模拟器的作用,通过各类场面的设置,诱发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小说虽然以情节取胜,但电脑作家的语言功底也不可小觑,该程序收录了19世纪至21世纪13位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知名作家的词汇和表达手法。据说出版社对电脑创作的初稿不甚满意,于是对初始材料进行了改动,随后电脑经过3天的“笔耕不辍”,创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第二稿。
(二)受众的反客为主
受众是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在面对视听艺术作品时,受众的角色已经不单单是信息的接受者,受众已经反客为主,成为二次创作者、意义的阐释者和完成者。在传统文本研究中,读者的地位已得到重视,而在数字时代的今天,读者的意义更是值得深究。
1.二次创作者安伯托•艾柯早在其《开发的作品》中提出“开放性”是艺术家和消费者的未来。“开放性”意味着创作者只是建构了一个作品的框架,它是未完成的、好比一座大厦只是完成了钢筋结构,真正的区隔划分、软装布置还需要靠受众来完成。康士坦茨学派创始人之一、德国接受美学理论代表人物伊瑟尔在其《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指出:“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阈的阅读期待,但唤起它是为了打破它,使读者获得新的视阈,如此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阈的文本结构,即所谓的‘文本的召唤结构’。”因为经验和想象的差异,每个人填补后对于作品的理解是不同的,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伊瑟尔认为“召唤性”是文学文本最根本的结构特征,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随时等待读者去想象、去补充,而其空白和不确定越多,需要读者发挥之处也越多,这样有限的文本就有了无限意义的生产可能。现在一些电影的文本就是开放式的,如电影《致命诱惑》,观众可以在内部预演时,通过按动座椅的按钮、给表演打分来选择最后的结局。现在还有一种以“机动观众”为特色的赛博戏剧,观众拿着遥控器随时在故事的进展过程中点击使之分叉,当剧中人分别走向两个方向时,观众还可以像游戏一样跟着某一个人物走,不同的人物会带来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创作者和受众在完成同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时,彼此交换了对方的大脑,同时也完成了交互关系。
2.意义的阐释者和消费者除了完成二次创作外,玩家更是意义的阐释者。在数字化的视听艺术作品中,意义是不确定的,结构也可能是多线性的,受众通过能动的参与不仅仅是对于意义空白处的填充,更是对于意义的阐释和延伸。“固定的作品结构被读者瓦解或重新构造了,意义也被新链接的文本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创造性的阅读使静止的结构被召唤式结构所替代,结构成了一种在‘运动’中不断发展的东西。”如台湾艺术家吴达坤的作品《迷楼———台北》就从影像、观看者、主体与自觉的角度出发,指明了当代人日趋异化的认知结构,也赋予“知觉的身体”一个讯息与媒体时代的漫游者形象,艺术家借此建构了“观者主体”的基础,自主性的体验、自我的阐释方式、互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心理投射,切入个体意识及群体关系的当代命题。在电子游戏中,玩家对于意义的阐释与完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是玩家自身;二是玩家在互联网中的化身,即玩家的赛博身体。化身是玩家在网络中的替身,它代替玩家去执行一切任务,在网络中所起的作用使多样玩家自身与化身关系密切。斯蒂芬森在科幻小说《大雪崩》中这样描述“化身”:“人物是由一种称作‘化身’的软件来支持的,他们是人们在元空间里用来相互交流的声像合一体。”玩家在刚开始玩游戏进入角色时,表演的是与自己截然不同的角色,时间久了必会把自己的个性带入到角色之中,原本与玩家无关的角色自然而然会被玩家自我内化,“这也是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其结果便是形成了角色与玩家之间的‘交互主体性’,玩家越是沉浸于游戏之中,与角色之间的融合程度就越强。就此而言,游戏本身对玩家的人格发展与转变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而角色最终的发展是创作者不能预料的。
二、结语
消费时代消费的、抽象的大众取代了具体的读者,这也契合了视听艺术作品出现的背景,例如增强现实艺术作品、增强虚拟艺术作品就是迎合了消费社会的需求,无论是谷歌推出的增强现实眼镜、TotalImmersion推出的虚拟试衣系统,还是迪士尼推出的增强虚拟游戏,其最终目的都是将受众变成消费者。
作者:魏佳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