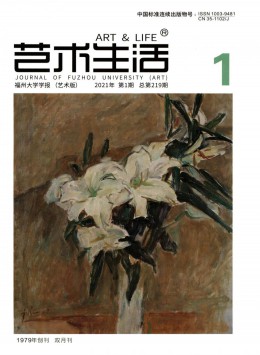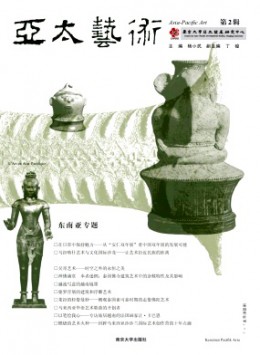艺术表现形式与情感关联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艺术表现形式与情感关联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本文作者:陈炎 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在西语中,形式(form)一词的来源颇为复杂,“其最接近的字源为古法文字forme及拉丁文forma———意指shape(形状、形态)。英文的form一直重复拉丁语系的复杂演变,其中有两个主要相关意涵:其一是肉眼可以见的或外部的形体,具有强烈的实体感……其二是基本‘型塑原则’(shapingprinciple)能将飘忽不定的事物化为明确、特定的事物。”[2](P147)不难看出,form的前一种意涵显示了“感性认识”的起点和源泉,form的后一种意涵则有着朝向“理性认识”的趋势了。在传统的认识论领域中,人们对“感性认识”这一复杂的知觉过程缺乏足够的重视,直到出现了被誉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加登。
鲍姆加登指出:“希腊的哲学家和教会的神学者曾经慎重地区别感性事物与理性事物。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把理性事物同感性事物等量齐观,因为他们以这名称尊重远离感觉(从而,远离形象)的事物。所以,理性事物应该凭高级认识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认识,而感性事物(应该凭低级认识能力去认识)则属于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Aesthetica)。”[3](P130)鲍姆加登认为,人类认识理性法则的高级认识能力和认识感性事物的低级认识能力应该分别属于两种科学来加以研究,前者属于逻辑性,后者属于感性学;前者面对抽象的范畴,后者面对具体的形式。在鲍姆加登之前,德国的唯理论者之所以忽视感性而重视理性,是因为他们觉得感性经验是混乱无序的,理性范畴则是明晰有序的。而鲍姆加登则指出:“混乱也是发现真理的必要前提,因为本质的东西不会一下子从暗中跃入思想的明处。从黑夜只有经过黎明才能达到正午。”[4](P15)感性认识作为理性认识的基础和前提,是发现真理的必要条件,因而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尽管鲍姆加登为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性而建立了所谓“感性学”,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仍然是将这一学科作为低级认识论来加以理解的。
那么,鲍姆加登的“感性学”又何以被理解为“美学”呢?在他看来,美的欣赏问题就是艺术的理论问题,而艺术理论问题就是感性的认识问题。所以,他在《美学》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如果说逻辑思维努力达到对这些事物清晰的、理智的认识,那么美的思维在自己的领域内也有着足够的事情做,它要通过感官和理性类似的思维以细腻的感情去感受这些事物。”“美在于一件事物的完善,只要这件事物易于凭它的完善来引起我们的快感。”[4](P2、43、288—289)在这里,与鲍姆加登相同的是,我们认为审美和艺术活动确实要面对的是具体的感性形式,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思辨;与鲍姆加登不同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审美和艺术活动是一种低级的认识活动,也不认为审美和艺术活动仅仅要获得的是一种感性“认识”的完善。
如前所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一种起于“形式”而终于“概念”的过程。“形式”是个别的、具体的,因而是丰富的;“概念”是一般的、抽象的,因而是明晰的。从前者上升为后者的过程,既是一个提纯、定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凝练、简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可以将纷纭复杂的客观对象纳入简单明晰的语言体系和逻辑框架进行认识和思考,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失去了许多微妙的感官享受与复杂的情感体验。所谓“茶素不是茶”,“酒精不是酒”,即如此。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种类的茶叶中提炼出共同的茶素,并以此完成对茶叶的普遍认识,但却不可能用提纯后的茶素来替代具体的花茶、绿茶、红茶、乌龙茶,更不可能从茶素中获得对黄山毛峰、西湖龙井、冻顶乌龙的真切体验。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种类的酒中提炼出共同的酒精,并以此完成对酒的抽象理解,但却不可能用提纯后的酒精来替代具体的白酒、红酒、黄酒、啤酒,更不可能从酒精中获得对山西汾酒、贵州茅台、四川五粮液的真切体验……因此,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形式”上升到“概念”、从“现象”上升到“本质”的过程,既是一种获得的过程,也是一种失去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感性认识”并不低于“理性认识”,也不仅仅是理性认识的初级阶段,而有其独特的价值。开掘这一价值,正是“感性学”(Aesthetica)的意义所在,也是“美学”(Aesthetica)的意义所在。
在我们看来,Aesthetica作为“美学”,并不是要追求什么“感性认识的完善”,而是要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体验。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对象既不可“意会”,也不可“言传”的话,便无法把握任何信息;如果我们的对象既可“意会”,又可“言传”的话,便会将其提升到概念、范畴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但是,无论我们的语言体系多么丰富、理论范畴多么完善,也总是无法将所有的感觉形式都上升到语言逻辑的范畴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总会有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需要表达,而这种表达的形式就是艺术。因此,面对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我们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情感体验,就像品尝一杯美酒、一壶好茶一样。因此,对于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来说,“形象大于思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说穿了,所谓“形象大于思想”,就是感性的艺术形式所承载的信息多于理性的逻辑描述,这也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无法被任何高明的艺术评论所取代的真正原因。
比如,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所画的不过是一个端庄而又美丽的妇女而已。但在她那神秘的微笑中,人们却可以感受到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以至于每一次看她,都会获得某种不同的感受:有时觉得她笑得舒畅而温柔,有时觉得她笑得严肃而矜持,有时觉得她的笑容略带哀伤和忧郁,有时又觉得她的笑容里暗含着讥讽和揶揄……围绕着这幅名画,学术界曾演义出所谓的真伪之谜、背景之谜、死因之谜、遗骸之谜、字符之谜、身份之谜。但说到底,还是人类的经验之谜、艺术的情感之谜。再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所写的不过是一群贵族男女的日常生活而已。但在他的描写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人生说不尽的喜怒哀乐、道不完的悲欢离合,以至于不同的人会感受到不尽相同的东西。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产生这种现象,既表现了读者角度的多样性,又反映了作品内容的丰富性。故从这一意义上讲,越是感性的内容、具体的形式,也就越丰富、越复杂。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一种“符号动物”。因为除人之外的其他动物都是靠天生具有的肉体机能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的,而人则不仅要靠天然的肉体机能,更要依靠后天对符号的学习和掌握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出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5](P34)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符号,应包含“能指”和“所指”两层含义。所谓“能指”,是指符号本身诉诸人们感官并能够加以辨别的色彩、形象、声音等表征形式;所谓“所指”,是指作为符号本身的表征形式所代表的事物、概念、意义。而“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例如,在交通规则上,人们把“红色”规定为“停止”,把“绿色”规定为“通行”,把“黄色”规定为“警示”;与之相应,警察在指挥交通时也会用不同的动作等表征形式来代表“停止”、“通行”和“警示”的“所指”意义;同样,警察还可以发出不同的口令,用声音这一“能指”来表达不同的意义。
对于人类来说,交通信号是比较简单、次要的符号系统,更为复杂和重要的符号系统是语言。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所面对的大千世界是感性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绝不会仅仅满足于直观地感受大千世界,而要把对象世界符号化。首先,人们要对客观事物加以命名,于是便出现了专有名词。比如,名字就是一种符号,“张三”、“李四”、“王五”,这些不同符号的“能指”所对应的“所指”就是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其次,人们不仅要对客观事物命名,而且要加以分类,于是在专有名词的基础上出现了具有概念性的名词。例如,我们发现了“张三”、“李四”、“王五”之间的共同点,把他们都称之为“人”、“男人”、“成人”等。与“人”、“男人”、“成人”这些概念相对应,我们还归纳出“狼”、“羊”、“草”之类的不同动物名词。“命名活动本身即依赖于分类的过程。给一个对象或活动以一个名字,即把它纳入某一类概念之下。”[5](P171)
如果说词汇是一种归纳抽象的结果,那么语法则使演绎推理成为可能。所谓语法,就是要使不同概念(词)之间的关系逻辑化。于是,我们在名词之外又有了动词、形容词、量词等;于是,我们便有了“人打狼”,“狼吃羊”,“羊啃草”之类的句子,即将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归纳逻辑’的创始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明确说过,语法是逻辑最基本的部分,因为它是对思维过程进行分析的起点。”[5](P162)有了归纳而来的概念,有了演绎而来的逻辑,于是就有了科学理论。“与科学的术语相比较,普通言语的词汇总是显出来某种含糊性,它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是这么模糊不定和定义不确,以致经受不住逻辑的分析。但尽管有这种不可避免的固有缺陷,我们的日常语词逻辑和名词仍然不失为走向科学概念之路的路标。正是运用这些日常语词,我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最初的客观视域或理论视域。”[5](P172)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理论科学的发达程度,既取决于概念的抽象程度,又取决于逻辑的缜密程度。正因如此,所有理论科学都有着由日常语言向专业语言乃至数学语言发展的趋向。因为专业语言比日常语言更精确,数学语言比专业语言更严谨。
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自然界的每一次进化同时也是退化,人类文明亦复如此。“从单纯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同意康德的话,数学是‘人类理性的骄傲’。但是对科学理性的这种胜利我们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科学意味着抽象,而抽象总是使实在变得贫乏。”[5](P183)大千世界原本是无限丰富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无限规定的总合。正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是,人们为了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必须在异中求同,舍弃每一个体鲜活的个性,从中归纳出抽象的概念。因此,这一抽象的过程,同时也是简化的过程。
譬如,所谓颜色,无非是长短不同的电磁波作用于我们视网膜的结果,这其间有着一个由明到暗、连续不断的谱系;但为了将人们对颜色的感觉符号化,只能将其归纳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所谓音高,无非是物体在空气中震动的频率作用于我们耳膜的结果,这其间有着一个由高到低的连续不断的谱系,但为了将人们对音高的感觉符号化,只能将其归纳为1、2、3、4、5、6、7七个音阶。所谓情感,无非是理智与意志之间形成的纠葛和张力,这其间既有简单的、单纯的情感,也有复杂的、矛盾的情感。但是,为了将对情感的表达符号化,人们只能将其归纳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有限的概念……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由经验上升为符号的过程,既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又是一个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这其中,有得亦有失。
不仅符号的形成如此,符号的运作亦复如此。我们说过,作为语言的符号运作,揭示了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使逻辑思维成为可能。但是,正像概念的抽象是一个简化的过程一样,逻辑的推理也是一个简化的过程。本来,万物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但形式逻辑只能在“质”上分为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在“量”上分为全称判断、特称判断和单称判断;在“关系”上分为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理由充足律等有限形式。因此,如果说概念之“言”不可避免地会漏掉一些生活之“意”的话,那么逻辑之“网”也不可避免地会漏掉一些经验之“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筌”的艺术便有了其用武之地。
首先,艺术所使用的媒介往往是具体的、生动的,如音乐中的节奏和旋律、绘画中的色彩和线条、舞蹈中的肢体和动作、雕塑中的材料和形状……从符号学的意义上讲,这些节奏和旋律、色彩和线条、肢体和动作、材料和形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能指”,因为它们自身并不规范,也没有明确的“所指”。然而,这些节奏和旋律、色彩和线条、肢体和动作、材料和形状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由于它们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能够引发人们的情感。分析起来,这些现象可能与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经验有关,比如,一个健康的、洋溢着生命力的形象自然会引发我们正面的情感,一个病态的、苟延残喘的形象自然会引发我们负面的情感;这些现象可能与人的生产实践有关,人类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培养了自己观察自然、感受世界的能力,从而对色彩、节奏、形状、运动有着极为细致的情感反应。这些现象还与人的社会习俗有关,比如红色和白色不仅有冷暖之分,而且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会引发人们不同的联想,有不同的功能划分。
由于这些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许多“对象”对于我们来说已不是纯然“客观”的了。正如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从经验上讲,事物是痛苦的、悲惨的、美丽的、幽默的、安定的、烦扰的、舒适的、恼人的、贫乏的、粗鲁的、慰藉的、壮丽的、可怕的。”[5](P100)如果我们把这些节奏和旋律、色彩和线条、肢体和动作、材料和形状也当作“能指”的话,那么它们所暗含的“所指”不是确切的事物或概念,而是复杂而精微的情感。在这里,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因而还不能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符号。正因如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多元的、复杂的、似是而非的,而不是清晰的、明确的、溢于言表的。这便是艺术作品“形象大于思想”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常常是超越民族和社会的。莫扎特是奥地利人,他所说的德语中国人听不懂,但中国人完全可以欣赏他那轻松而又欢快的《小步舞曲》;阿炳是中国人,他所说的汉语外国人听不懂,但他那凄楚而又悲凉的《二泉印月》却完全可以引起外国人的情感共鸣。总之,如果说艺术也是一种语言的话,一方面,这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模糊的、暗昧的;另一方面,这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
其次,艺术创作的法则常常是跳跃的、非逻辑的。艺术家往往利用想象和联想、隐喻和象征等方式将音乐中的节奏和旋律、绘画中的色彩和线条、舞蹈中的肢体和动作、雕塑中的材料和形状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形象和作品,而不是依靠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由于艺术创作既没有固定的语法,也没有缜密的逻辑,因而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符号行为。所以,人们常将艺术活动称之为“形象思维”,而与科学活动中的“逻辑思维”相区别。事实上,艺术家对各种材料的运用也确实不需要遵从形式逻辑,而需要遵从情感的逻辑,即在符合情感表达的基础上对材料加以组合,对形象加以塑造。贝聿铭为什么要在卢浮宫前建造一个玻璃金字塔式的入口?乌特松为什么将悉尼歌剧院建造成白帆或贝壳的形状?这一切很难用逻辑和推理说清楚。或许,正是由于艺术创作活动是超越逻辑推理的,因而艺术家很难按照某些规则训练而成;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艺术的“语法”非约定俗成,因而可以获得超越民族、超越时代的普遍认同。
人们也许会说,上述艺术类型中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门类———文学,而文学恰恰是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因而需要特别说明。不错,包含诗歌、散文、小说在内的文学是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但即使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也是要借助语言来超越语言、通过概念来超越概念的。“这一点,只有当诗人具有把日常语言中的抽象和普遍的名称投入他诗意想象力的坩埚,把它们改铸为一种新的形态时,才是可能的。他由此便能够表现快乐和忧伤、欢愉和痛苦、绝望和极乐所具有的那些精巧微妙之处,而这却是其他所有表现方式所不可企及和难以言说的。”[5](P109)一方面,文学语言往往比日常语言更丰富、更复杂、更精致,即通过形容、比喻、象征、夸张、对偶、排比、拟人、通感等各种复杂的修辞手段对客观世界和主观心理进行更加透彻和细腻的描写;另一方面,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常常采取陌生化、反常规、超逻辑的手法突破日常语言的修辞方式和语法规则,从而形成对传统符号体系的挑战。
譬如,如果用逻辑思维的标准来看,我们很难说清楚“人闲”与“桂花落”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但如果用形象思维的标准来说,“人闲桂花落”无疑是一句绝妙的好诗。如果用逻辑思维的标准来看,我们很难说清楚“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定关系?尽管从汉代以降,便有很多学者对此作过各种各样的研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至今也没有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因为说到底,这些研究和解释都是以逻辑思维的方式入手的,而艺术创作则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进行的。按照康德的认识论原理,只有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纳入十二个范畴时,它们之间的关系才是可以被认知的。而在我们看来,当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纳入有限的逻辑范畴时,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被明确地认知,但却同样可以被感受。这种感受的方式便是审美和艺术。因此,就像卡西尔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伟大的诗人都是一伟大的创造者;不仅是他的艺术领域的创造者,而且也是语言领域的创造者。他不仅具有运用语言的膂力,而且还具有改铸和创新语言的膂力,把语言注入一新的模式。”[6](P107)元代文学家马致远曾做过一首《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如果从逻辑思维的角度出发便很难理解这首词的真正含义,故只有从形象思维的角度入手才能真正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人生经验和丰富的情感内涵。
其实,不仅诗歌如此,即使是在小说、散文等具有相当长度的叙事文体中,文学家也不能仅仅按照逻辑思维的方式谋篇布局,而是要按照形象思维的方式进行创作,以达到“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叙事效果。当然,在具有叙事成分的文学作品中,人们会获得很多的人生经验,因而其创作又必须符合一定的生活逻辑。对此,美国学者杜威曾经下过“艺术即经验”的断语。然而,细加分析便不难看出,“经验”之所以不同于“经历”,还在于其中所包含的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例如,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每一个人物的动机、愿望、理想与其所处的环境、条件、地位之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在“意志”与“理智”之间会形成错综复杂的“情感”,这里面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有肝胆相照、义薄云霄!而每一个读者的主观意愿又会与作品的实际内容之间产生必要的张力,使我们对其中的人物产生或尊敬、或爱慕、或鄙视、或憎恶的情感,期许他们的未来,牵挂他们的命运,甚至废寝忘食地沉浸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而如何编排故事的情节、如何塑造人物的行为、如何调动读者的兴趣,也不仅仅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在这里,感情的逻辑仍然重于思维的逻辑。
总之,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音乐中那梦幻般的节奏和旋律、舞蹈中那超越生活的肢体和动作、绘画中那高度夸张的色彩和线条,还是诗歌中那陌生化、反常规、超逻辑的语言,都旨在使人们从惯常的逻辑思维和异化了的现实生活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以获得一种超越语言描摹的心理慰藉。正像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人的感性变得愚钝了:人们仅以事物在现存社会中所给予、造就和使用的形式及功用,去感知事物;并且他们只感知到由现存社会规定和限定在现存社会内的变化了的可能性。因此,现存社会就不只是在观念中(即人的意识中)再现出来,还在他们的感觉中再现出来。”[7](P132)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艺术作为“美学”的承载者,有着更新人们感性经验和情感世界的特殊意义。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并不是所有的全能上升到理论的水平和概念的层次,比如我们可以敏感地观察到一个人的面孔转悲而喜的微妙变化,但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一块肌肉、哪一条皱纹体现了这种变化;我们可以敏感地察觉到一个人时而痛苦时而欢愉的呻吟,但很难说清究竟是哪一个音符、哪一种旋律承载了这种情感。而艺术家则不同,他们不仅有着比普通人更加敏锐的观察和感受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对肌肉和线条的组合、对音响和旋律的搭配而将这种微妙的情感扑捉、再现甚至创造出来。于是,便有了惟妙惟肖的雕塑和如泣如诉的音乐;于是,便有了传神写意的绘画和动人心魄的舞蹈。
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艺术,就是对人的生活经验的浓缩和情感体验的再现。只是,与科学家不同,艺术家不是使用逻辑严谨的规范性符号,而是运用具体生动的感性材料,如线条、色彩、动作、节奏、音响等。正因如此,人们常常习惯用一种比拟性的说法,来指称所谓“肢体语言”、“音乐语言”、“绘画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艺术都可以被看作是语言,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罢了。它并非一种言语符号的语言,而是直观符号的语言。那种不能感受色彩、形态、空间形式和类型的人,遂被排除在艺术作品大门之外;由此,他不仅被剥夺了审美快感,而且还丧失了向最深层的实在切近的可能”[6](P134—135)。
既没有固定的词汇,也没有严格的语法,那么艺术家是怎样利用这种“特殊的语言”来实现自己的创造呢?与科学家从物质现象中抽象出概念相类似,艺术家也需要对生活经验进行一定的抽象,只是这种抽象不是指向逻辑范畴,而是始终保留在经验世界里。以绘画为例,一个真正的画家并不是事无巨细地描摹对象,而是要用最为简洁、最为有力的笔触将对象的情感特征呈现出来。正因如此,画家笔下的线条才能比常人手中的线条更准确地把握客观对象的形态和表情,画家笔下的色彩才能比日常生活中的色彩更突出地体现对象的特征和个性。以舞蹈为例,一个真正的舞蹈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还原生活中的各种动作,而是用最为美妙、最为动人的动作将主观的情感内容呈现出来。正因如此,舞蹈家的行为举止才会比常人更有韵味,举手投足才会比生活更加精彩。同样,在这种类似披沙拣金的努力中,音乐家从杂乱无章的音响中“抽象”出美妙的旋律,文学家从纷纷攘攘的词汇中“提炼”出动人的言词。
这种“抽象”和“提炼”,既需要一定的生活经验积累,更需要一定艺术技巧的长久训练。在生活经验的积累方面,由于“情感”是产生于“意志”与“理智”之间的“关系质”,因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有足够的生活经验:既要理解不同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生活情趣,又要懂得人生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历史的规律,从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最生动、最形象、最有典型意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一点,在叙事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中尤为重要。在艺术技巧的训练方面,由于“情感”是通过“形式”来加以呈现的,因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具备娴熟的艺术技巧:既要对形体、线条、颜色、音响、节奏、语言等各种感性材料有高度的敏感性,又要有驾驭这些材料的能力,从而在杂乱无章的感官材料中“抽象”出最形象、最动人、最美妙的艺术形式。这一点,在叙事性较弱的音乐、绘画、舞蹈中尤为重要。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既要深入生活,体验人生的喜怒哀乐,又要加强训练,掌握艺术的各种技巧。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说的是前者;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说的是后者。
这种“抽象”和“提炼”的结果,便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英国艺术家克来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指出:“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的关系,激发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视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艺术的共同本质。”[8](P4)在这里,“形式”和“意味”之间的关系,犹如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约定俗成的,“形式”和“意味”之间的关系则是隐晦的、令人回味的。事实上,“形式”背后的“意味”并不是别的,而是“情感”。在艺术中,由于那种特殊的、微妙的情感不能够用有限的概念加以表达,因而只能借助于“形式”,或者说由“形式”组成的“形象”来加以呈现。于是,“形式”和“形象”便成为艺术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形式”和“形象”承载着“内容”与“情感”,它们之间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从消极的意义上讲,任何艺术品都必须有“形式”,抽象的艺术品是不存在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一部作品美学价值的高低之别,不在于“形式”是否繁杂,而在于这一形式的背后承载了多少“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