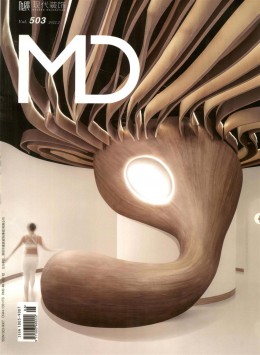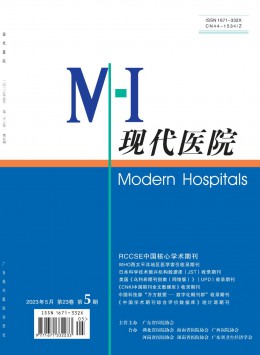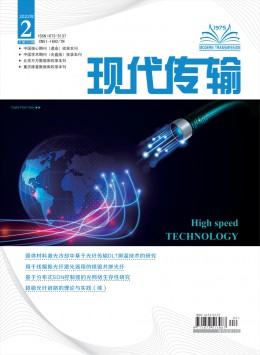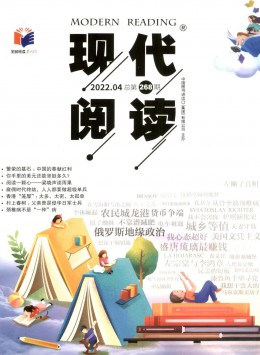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艺术形式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艺术形式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表现主义画家保罗•克利这样说过:“一个真正艺术家不断追求和为之奋斗的应该是艺术的形式,它比独创的灵感更为重要。形式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艺术家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驾驭它。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它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健全的神经。”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吸收借鉴了西方素描和解剖的知识,强调尊重对象,以人为本的精神,经过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和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画教学思想实践,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日渐发展成熟,在形式内容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认识。“造型”这一具体称谓来自于西方绘画理论,但早在中国古代便已有关于“形”的理念论述。中国的“形”与西方的“造型”,虽有共通点但不可等同。一幅现代水墨人物画应有一定的艺术效果和艺术感染力,而非机械地反映对象,导致作品了无生机、死板僵硬,如何做到“气韵生动”?需要通过画面上的人物形象来体现,必须凭借“形”去体现,这种“形”是生动的“形”,有艺术力量的“形”。要去表现这样的“形”就需要在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中结合扎实的造型方法。这种适合现代水墨人物画而出现的造型手法是随着西方素描系统的引进和对我国古代绘画理论研究后应运而生的,它需要作者更进一步地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律、生长规律等,不但要表现出外部特征,还要表现出形成这些外部特征的内在规律。法国19世纪画家安格尔看待造型的角度不妨作为学习借鉴,他提出:“形——这是一切的基础和条件。即使烟雾也必须用线来表现。”要画好水墨人物画,光有写生的造型能力还是不够的。它还要求画家要有主观想象塑造造型的能力。安格尔又指出:“你们蓄意要表现的形象应该先在你们的头脑里整体地展现在眼前,当你们描绘形象时才能和你们早在构思中已经掌握好的形象一样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画的造型,由于材料——毛笔、墨汁、生宣纸的特殊性能,也要求造型能力必须高度熟练。离开高度熟练的造型能力,要随手挥毫是办不到的。有些画家画水墨人物画时之所以能轻松自如,一挥而就都是以其极为熟练的造型能力作为发挥笔墨效果的基础保证。另外,中国画还比较注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之似”就是要求不在表面上过多地,片面地追求,而主要追求内在的精神实质。从而达到更为真实地反映对象的目的,不要“谨毛而失貌”,这与加强写实能力不相矛盾。“不似之似”是生活形象与艺术形象的同意和辨证。“不似之似”正是为了“似”,而不是似是而非。片面地理解会导致认识上以为中国画造型能力弱不要紧,将“似与不似”生硬的套用这里,这是片面且错误的。“不似之似”要求作者尽力去反映和表现事物的本质,突出反映对象的特征所在,从而达到“似”的目的。“不似之似”要求作者从事形象的塑造时要处于主动地位,要有自己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趣味的追求。所以,它要求创造的艺术形象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象,又是作者的主观认识,从而作品获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李可染说过:艺术家对客观现实应是忠实的,但却不是愚忠,真正忠于生活的结果,是主宰生活。
一、形式之笔墨
中国画从技法角度而言,实质上就是如何用笔用墨的问题。中国大约自11世纪开始,“笔墨”的含意就不仅是工具的名称,还成为中国绘画技法的代名词。有规矩始成方圆,笔墨就是中国画的规矩。中国画以其特有的笔墨技巧作为状物及传情达意的表现手段,以点、线、面的形式描绘对象的形貌、骨法、质地、光暗及情态神韵。这里的笔墨既是状物、传情的技巧,又是对象的载体,同时本身又是有意味的形式,其痕迹体现了中国书法的意趣,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由于并不十分追求物象表面的肖似,因此中国画既可用全黑的墨,也可用色彩或不同墨色结合来描绘对象,水墨所占比重相较色彩更多,所以中国画又称为水墨画。不同墨色概括总结为墨分五色,浓淡干湿焦,或焦浓重淡轻,以调入水分的多寡和运笔疾缓及笔触的长短大小的不同,造成了笔墨技巧的千变万化和明暗调子的丰富多变。同时墨还可以与色相互结合,而又墨不碍色,色不掩墨,形成墨色互补的多样性。南齐谢赫的六法论提到“随类赋彩”,以墨为主的中国画注重对象的固有色,而光源和环境色并不重要,一般不予考虑,但为了某种特殊需要,有时可大胆采用某种夸张或假定的色彩。笔墨问题一直被历代画家、评论家予以重视。五代后梁的荆浩认为吴道子“有笔无墨”,而项容“有墨无笔”,皆美中不足;明朝董其昌的“画岂有无笔墨者”。石涛的《画语录》中有一段专门论述笔墨。“古人有有笔有墨者,亦有有笔无墨者,亦有有墨无笔者;非山川之限于一偏,而人之赋受不齐也。墨之溅笔也以灵,笔之运墨也以神。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石涛在分析笔墨的运用方面有意将笔与墨分开,他所指的笔倾向于用线造型,描绘客观事物,而墨倾向于渲染气势,加强主观效果。“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他认为“墨”离不开“蒙养”,就诸多人对“蒙养”一词的解释综合来看,“蒙养”大意是指个人的世界观与修养,也就是说“墨”离不开画家本身对生活的体验与对世界的认知;“笔”离不开“生活”——客观事物的造型基础。“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石涛对之前古人中“有笔有墨”“有笔无墨”及“有墨无笔”的现象作了解释说明。谈到了光有主观认知而无法塑造客观的形象,即是“有墨无笔”;而单有客观造型却没有主观的组织刻画,即是“有笔无墨”。这与现代水墨人物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现代水墨人物画不同于传统水墨人物画的特点之一,是受到了西方素描与解剖知识的影响之后,在塑造人物方面不同于以往,而是更加尊重人物造型本身,正如石涛所谓的“生活”,但是作为中国水墨画,又不能单单强调刻画对象本身而忽略了中国特色的水墨语言,变成了单纯用中国的毛笔画西方的素描,这时就需要画家本身的“蒙养”来加以主观创作。如何解决“笔墨”关系,这也正是现代水墨人物画发展中所不能避免且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石涛在“笔墨章”中提出的用“笔”构造形象,用“墨”渲染气势给现代水墨人物画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启示。傅抱石语:“脱离时代的笔墨,就不称其为笔墨。”除了笔墨,中国画的题材内容也是值得反复琢磨的。作为现代水墨人物画,单从字面上来看,现代性是它的特点之一。而现代中国社会各界非常重视民生问题,艺术当随时代,这一题材更成为中国水墨人物表现题材的重中之重。
二、形式之题材
不同的题材决定于作者对所表现对象的认识和感悟,每个人的认识角度不同,又受各自的生活环境,生长经历影响,所以不可能完全一样。石涛在其《画语录》“尊受章”中提出“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石涛谈到了感受与认识的关系,他提出感受在先而认识在后,先有认识而后感受,就不是“纯粹的感受”了。现代水墨人物创作中刻画人物,第一要做的就是观察对象,抛开素描解剖这些理性的知识,以画家特有的敏锐感受,抓住对象给予的直观感受,之后再加之理性的分析去完善塑造对象,这样的水墨人物作品才能包涵画家本身倾注的情感,反之则是空洞乏味。按石涛的理解,是缺少了“蒙养”,也就是缺少了生活体验,这些作品就成为了“有笔无墨”的作品。“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画的根本是“心”,是画家的“受”。石涛在尊受章中突出强调了尊重自己感受的重要性。他在远尘章中再次提到“画乃人之所有,一画人所未有。”人人都可以作画,却不理解要根据自己的感受作画。尊重自己的感受,这一点在现代水墨人物画创作中是必须重视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在石涛看来,古人的须眉和肺腑,不可能生长到“我”的身上,即便有时碰触了某家,那也并不是“我”特意然之,而是同一事物对不同画家启了相似的灵感,绝非泥古不化。中国画讲求传承,无承继何以谈传接?那么学习中国画,是要以临摹古人为重还是以写生现代为主?吴冠中在《我读石涛画语录》中结合自身的经历谈到:“从临摹入手多半坠入泥古不化的歧途。必须从写生入手才能一开始便培养学生对自然独立观察的能力,由此引发出丰富多样的表现方法。”而丰富多样的表现方法难免的会与古人有碰触,石涛并未否认这样不行,但是他强调“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故君子惟借故以开今也”。现代水墨人物画学习离不开对古人作品的临摹,借古开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临摹学习的前提,不能一味的“拿来主义”,否则现代水墨人物画还谈何“现代”?
三、形式之构图
在构图上,中国画讲求经营,它不是立足于某个固定的空间或时间,而是以灵活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限制,把处于不同时空中的物象,依照画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创作的法则,重新布置,构造出一种画家心目中的时空境界。于是,风晴雨雪、四时朝暮、古今人物可以出现在同一幅画中。因此,在透视上它也不拘于焦点透视,而是采用多点或散点透视法,凭借以或上下,或左右,或前后移动的方式,观物取景,经营构图,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同时在一幅画的构图中注重虚实对比,讲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徐悲鸿在中国画实践中引入焦点透视,这项贡献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他在中国画改造的过程中所动用的透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线性焦点透视法。画面中的视平线不是随意设置,而是严格的归结为一条,这就与中国古代的“高远法”、“平远法”等流动的观察方式和在地平线的上下自由移动的构图方式拉开了距离。艺术发展受时代环境所影响,中国的建筑一直在发生变化,鉴于古代传统房屋高梁的特点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古代绘画的规格为适应环境与古人的审美需要,一般主要为挂轴或手卷或册页等形式,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人民居住环境的改变,使绘画创作规格不再拘于挂轴,手卷等形式限制,巨型尺幅的佳作频频出现,正是归功于焦点透视法的引用使得现代水墨人物画在创作大幅尺寸时的构图有的放矢,使之笔墨造型在此基础上得以充分表现发挥。
四、结语
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推进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画由过去士大夫和贵族娱乐自赏的贵族艺术转向为“民众的艺术”,画家们将视角投向社会现实,使中国画在题材内容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水墨人物画如何造型,如何把自然对象转换为笔墨语言,转换为水墨造型,得意而不忘形,丰富水墨人物画的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作者:邬树乙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