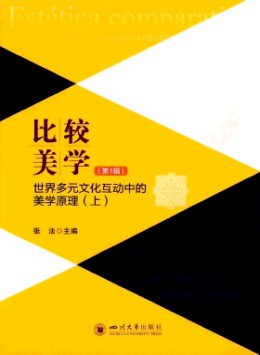美学视野下中国园林艺术探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美学视野下中国园林艺术探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影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其最基本也是高的审美原则。其以自然为蓝本,将花木、山水、建筑等元素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内,“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小见大、虚实相生以期创造出“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之咫尺山林。正是在中国古典园林所创设的这种独有的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中,除了供人们以可游、可居之外,其更多地为主体提供了一个诗意的心灵栖居之所,在其中,人与自然达到了更高、更深层次的契合,作为审美主体的自我多了一份与所处世界并生共存的感悟。
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艺术性创构
自古以来,“崇尚自然”是中国人的天性之所归,也是中国艺术创构之理念。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自然乃万物之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到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之“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等。“道法自然”作为中国人观照世界所建立起来的哲学思考,一直影响并指导着中国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思维,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艺术性建构,是秉承“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的体现。可以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理想,是创造园林艺术、园林美的内在依据,也是构成中国园林艺术民族特色的根本之所在。而这种天人关系与西方和阿拉伯的造园体系相比,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西方和阿拉伯的造园体系中“,人”作为中心,是以征服自然、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的,人与自然形成的是一种对抗关系,通过人为的干预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与人达到和谐,处处折射出人的力量。相形之下,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园林审美的主体意识是包含在自然的形式之中的,是在自然中见出主客体的和谐,或者说,更像是人与大自然通过造园方式所进行的一场情意绵绵的对话,是人怀念自然这一人类故乡之美的“诗篇”。中国园林艺术的“天人合一”大致上可以归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将“天人合一”统一于主体,通过景物的人格化,即山水“比德”来实现。简言之,便是“自然的人化”。另一类则是通过“与物化一”使主客体和谐统一于人与自然共同的本体“道”,即“人的‘自然’化”。此时的自然,已不同于狭义的自然万物,而是“自然宇宙大化”。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论是造园角度,还是从园林审美角度,中国园林艺术“天人合一”之类型,前者相当于王国维所谓“以我观物”,为“有我之境”,后者则是“以物观物”,为“无我之境”。园林作为“人化的自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从造园者的角度而言“,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唐志契《绘画微语》)。园林的风貌,也总是由于造园家个人性情、审美情趣及个人对自然和社会理解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因此,园林中的山水、花草之美,才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的形、色、声、光、香,景物之中还积淀着某些超越物象之外的审美信息,比如象征、比德,就是造园家个人性情志趣的侧面折射,其根本在于园林是“人化的自然”。通常的园林是造园家“胸中丘壑”的物态化、形象化、典型化的意象再现,而非纯粹自然的再现,从而成为“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写意山水园林艺术品。另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鉴赏过程中所表现的主体意识,不过这种主体意识的介入要含蓄得多。宗白华有言:“中国人看山水,不是心往不返,目极无穷,而是‘返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同任何文学艺术相关的审美活动相似,园林的审美的本质亦在于审美主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肯定,而非自我牺牲,不是被动的‘反映‘’接受’,而是依靠人的主动性所进行的审美发现与创造,从而达成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趋同。好像苏轼说的“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人的‘自然’化”,并非是将造园主体或鉴赏主体的审美意识,形象化地呈现出来,其关键在于,这里的“自然”作为更高一层的审美范畴,并非狭义的物质自然,而更多地倾向于道家的“自然”,形而上的“自然”。张彦远将画分为五等,“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神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所谓“自然”者为上品,反映在中国园林艺术中,则是造园者、园林观赏者可以“同自然之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可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可以“凝神遐想,妙悟自然”主体可以在园林所创设的“咫尺山林”中,突破有限的园林山水,有所觉解和体悟,把握更深层次,更加丰富、蕴藉的自然之道,这应该才是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最应该珍视的东西。中国园林艺术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双向建构起来的,并且在更高的审美层次“人的‘自然’化”中得以升华,呈现出艺术性,这种艺术性便是对“天人合一”的复归。
二、自我与世界并生共存关系的感悟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域中“,作为此在的世界领会是自我领会”,即“此在”作为此时此地的我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我,世界也总是我存在于其中的、使我成其为我的世界,因而,自我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具有了动态性的同一关系,此在即意味着对世界、对自我的双重领会,且对世界的领会和对自我的领会共时性地发生。这里的世界,不仅仅包含形形色色触目可及的在场的客观世界,更包含有那些在主体的主观想象、领悟中的不在场的主观存在世界,它是一个对此在主体来说主客统一的世界。而只有置身于这种自我与世界共生并存的关系之中,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才是充实且充满诗意的。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尤为如此。中国古典园林除了供人游、居之外,它更多更高的旨趣,就在于以充分艺术化的时空形态手段,建构出诗意隽永的心灵居所,也就是文人雅士们理想的诗意栖居之所。不同于古典的文学、艺术,它除了自然山水之外,同时集中国传统的建筑、书法、绘画、雕刻、音乐等为一体,以其优美的生态环境、雅致的人文环境与中国人心性中对“宇宙”的终极思考及审美无功利的人生境界相结合,蕴含了人类最高的生存智慧——咫尺园林,天地境界。泰戈尔在《神的意象》一文中这样说:他寓居于一个历史的宇宙里,他经常处于记忆的连绵环境里,一般动物唯有透过种族的延续才能在时间的洪流里留下痕迹,而人类却能依靠着自身的心灵,独步于天路历程。他这种知识及智慧的巧妙所在,正在于他们能将自身的根溯源自亘古的往昔,并将自身的种子散布于浩瀚的未来。此外,人类还能在他内在实现的领域里,建立一种非物质价值的栖身之所。当它的心灵涉身于这个世界时,他的意识正像一颗种子一样,静静地等待着萌芽的时机,俟时机成熟时,个人便能在他的宇宙大我里,实现了自身的真理。徜徉于中国园林的烟柳长堤、草木山水之间,获得的不仅是物质的栖身之所、简单的审美直观,更是在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世界对话中,对于自我,对于生命审美境界的获致,这也正是中国园林通往哲学向度的更深层次思考。如苏州网师园有一处以“真意“命名的门景。透过这处门景,恰巧可以透视出邻院中由曲桥、水池、古柏、回廊等丰富景物所组成的景观序列,而粉墙的舒展雅洁又很好地衬托和突出了背后纵向展开的景观内容,仿佛一幅内容饱满而层次分明的水墨画铺开于干净、素雅的宣纸之上。除此之外,更为点睛的一笔是“真意”这一题额,使此处园林境界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升华“。真意”出自陶渊明《〈饮酒〉其五》,原文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真”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唐荆浩的绘画理论就有“度物象而取其真”,历代园林也经常以“真意“”真趣”这些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作为园林构景的旨趣之所向“。真”在《庄子•秋水》篇中,以形容保持质朴自然而未被人为规范所羁绊束缚的一种生命状态,而之后,成为在生命伦理学和美学上的重要命题。如苏舜钦《沧浪亭记》就说:自己在这座园林之中的“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距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乃是一种充满“真趣”的生活和审美方式。而这应该也是陶渊明“欲辩已忘言”的“真意”之所在。至此,在此处园林盛景中,个体早已从一个冷静的理性旁观者,渐渐地融化成园林画卷中的一片绿叶,一汪清泉,亦或是一块耸立的异石。此时此刻,个体不再是孤独的,渺小的,已消溶在无际的大地大化之中。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所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个体自我已与天地世界浑融,彼此难分,有自我对在场客观存在的空间的直观,更有对不在场之本真“大意”的顿悟。再如苏州留园中的“闻木樨香亭”、广州馀荫山房的“闻木樨香轩”“。闻木樨香”已经成为宋代以来园林的一个常用的主题,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苏州“渔隐小圃”等园林中也都有表现这一主题的景观建筑,在大多数的观赏者看来,这里不过是南方园林中为秋季品赏桂花(木樨)姿态和异香而设的景点。实际上“,闻木樨香”出自哲学上的一个典故:宋代的黄庭坚探究哲学和禅学的深意,晦堂禅师告诉他:“道”这个哲学本体虽然深刻,却又是显豁而“无隐”的,黄庭坚对此总是不得其解。秋日一天,黄庭坚和晦堂禅师同行于山间,当时正值岩上桂花盛开,于是晦堂问他是否闻到了浓郁花香,并告诉他“道”的形态亦如花香一般,虽然不可见,但是上下四方无不弥漫,所以“无隐”。“无隐山房”等景点,其立意都在于袭用这个典故而表明审美者对哲学本体那种丰盈充溢、沁人心脾之存在状态的理解,景观建筑因而似木樨香般,突破有限时空,获得最大化的审美张力。自我与世界便在此审美境域中并生、契合。笔者以为,要深刻理解一切艺术的前提是,要在依托具体时空形迹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艺术眼光乃至心性之光的支点,就是要通过一个有形的入口进入到生命旅程和无限宇宙长河的脉络之中。而中国园林艺术应该是中国哲学和文化视野中最理想的具体时空形迹,正是有了这一具体而充分的艺术化窗口,我们才能够真切地体认、参悟自我生命在宇宙运行中的位置和价值,从而自我的生命以一种具有哲学意趣的向度和界域,栖居于审美化的宇宙大化之中。
作者:张敏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