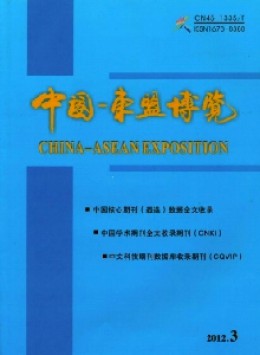中国文脉的语言艺术探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中国文脉的语言艺术探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中国文脉》的语言轻重缓急、端严生动、长短句错落有致,使《中国文脉》所展示的悠久文学史就像瑰丽绮美的画卷,给人以“浓妆淡抹总相宜”之感。《中国文脉》中的对比、比喻、排比、反问、引用等修辞手法的大量使用,使读者生动形象地感受到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的气韵。幽默诙谐的语言和现代流行词汇的使用是《中国文脉》的一大特色,作者如此运用,打破了时空距离的遥远之感,使读者跟历史文化和谐而亲近。哲理性的思辨、雅俗共赏的语言、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使《中国文脉》具有独特的语言艺术特征。
关键词:《中国文脉》;语言艺术;特征
一、工笔的技法历史的画卷
《中国文脉》的语言如同工笔,用细致的笔法,一丝不苟地为读者描画出清晰的中国文化脉络,有重有轻,有密有疏,有粗有细,有急有缓,色彩纷呈。《中国文脉》在语言的运用上,精确而深刻,华美而简洁,长句和短句错落有致、恰如其分、扼要明了。丰富多彩的语言使《中国文脉》所展现的中国文学史舒缓而宁静地流进读者的心田,其所洋溢的鸿蒙而壮阔的诗情画意又深入人心。
(一)语言精警恰切
《中国文脉》用精准的语言,有深度地阐述中国悠久的文化史,使读者认识准确,感受深刻。“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1]这里作者首先明确“中国文脉”,以便读者对作品有准确的理解和认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使读者对“文脉”进行准确的定位,不至于在之后的阅读中混淆其意。照理,文物专家不懂文脉,亿万富翁不懂文化,十分正常。但现在,现代传媒的渗透力度,拍卖资金的强烈误导,使很多人难以抵拒地接受了这种空前的“文化改写”,结果实在有点恐怖。[2]“文化改写”一语中的语言精确深刻,表现出作者对国人认识中国文学现状的忧思,进而有广度、有深度地阐述厚重的中国文学史。绵长而辉煌的中国文学史,通过余秋雨哲人的思辨、文化的良知、严谨的态度、精准的语言为读者展现出来,内涵丰富,赏心悦目。
(二)语言精当简洁
《中国文脉》语言准确、精辟、深刻,但也不缺少简约、朴素、生动。作品对历史文人的成就和地位则运用简洁而概括性的语言,恰如其分地突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和文人个性。陶渊明创造了一种以“田园”为标识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不仅如此,他还在这种“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个“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华文化圈内可能无人不知,把一个如此飘渺的理想闹到无人不知,谁能及得?[3](辛弃疾)他在朱熹走后七年去世,一个时代的高层文化,就此垂暮。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我心中整个中国古典文脉的黄昏。[4]准确、简约、生动的语言使古代文人跃然纸上,特点突出,个性鲜明,读者一目了然。精简的语言使《中国文脉》独树一帜,其所呈现出的中国文学史更加简洁而完整、生动而厚重。
(三)长短句错落有致
“史”给人一种厚重、枯燥等特点,文学史也不例外。非专业的读者通过史书了解中国文学史是有一定的难度,《中国文脉》则为普通读者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中利用汉语的四声节奏体现语言的音乐美,主要表现为长短句的运用。“现在社会上经常有人忙着要把那些该由博物馆保护的文化遗产折腾到现实生活中来,而且动静很大,我就很想让他们听听元杂剧轰然倒下的壮美声响。”[5]作者用较长的语句阐述历史的厚重和反思。也有一些如同演讲性的语言,简洁明快,读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一种阅读上的愉悦。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6]面对这两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键翅已远,残羽充鹏。”[7]这样的语句在《中国文脉》中比比皆是,具有严谨性、知识性和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如同我们在聆听作者的讲述,时而铿锵有力,时而语气舒缓;时而义愤填膺,时而态度温和。语言的轻重缓急、端庄生动,长短句错落有致,使《中国文脉》所展示的悠久文学史就像瑰丽、绮美的画卷,给人一种“浓妆淡抹总相宜”之感。
二、修辞的巧用历史的再现
修辞手法的使用是秋雨先生作品的一大亮点,《中国文脉》也不例外。表面上看,大幅度的修辞使用,似乎显得文章太过于华丽而奢靡。但作者在华美的外表下,实则是从深层表现出对中国文学史的崇尚和对各朝大家的崇敬,使漫长丰富的文学史生动、形象地毕现;使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个性鲜明,有血有肉,就如同我们身边的朋友、邻居,甚至亲人,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一)对比
对比手法是文学创作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创作手法,能够使文章更富感染力,艺术效果更强烈。在《中国文脉》里,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对比,使文章的语言极富抒情性,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中国文脉》中有人物的对比、有作品的对比、有文学样式的对比、有欣赏者对文化认知的对比。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相比之下,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8]秋雨先生在文脉一开篇对先哲老子和孔子做了对比,既突出两位先哲学说的特点,又表达出独到的人文情怀。他不太像执掌文脉的人,但他执掌了;他被官场放逐,却被文学请回;他似乎无处可去,却终于无处不在。[9]通过对比肯定“屈原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中国文脉中的作用。对比在文中运用得最多。有西方文脉和中国文脉受“北方蛮族”影响结果的对比;有老子和孔子、《诗经》与《离骚》、汉赋与《史记》、司马迁与唐宋八大家、曹操与诸葛亮、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李清照与蔡琰的对比;有元杂剧和古希腊悲剧、古印度梵剧之间的比较;有元杂剧与明代传奇、清代京剧的比较;又有《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的对比。说到南北朝的文化,首先以文友蒋勋和“我”崇尚的南北文化的对比。谈到唐诗的顶峰,以王勃、张若虚与李白、杜甫进行比较,说明李白、杜甫时期的唐诗是“顶峰上是顶峰”。作品以对比的形式彰显中国文脉的特质、名作的特点、大家的特性。让读者看得清楚,理解得透彻,收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二)比喻
通过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可以使深奥的道理浅显化,使具体的事物变得更加形象化,冗长繁琐的说明简洁化。既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又便于深入的理解。《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10]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唐初,这种文风(骈体文)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11]《中国文脉》里比喻的大量使用,使原来深奥抽象的文学史具体地显现出来,从而使文章的语言才情横溢、文采斐然。
(三)比拟
比拟使文章表意更加丰富,抽象的历史生动形象,历史中的“人”或“物”色彩鲜明,读者会产生丰富的联想,有着对历代文学名人的强烈感情,引起共鸣。李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政脉”与“文脉”是两件事。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在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确实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之中,明月夜风知道:中国文脉光顾此处。[12]元杂剧即使衰落也像一个英雄,完成了生命过程便轰然倒下,拒绝有人以“振兴”的说法来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13]比拟在文章中的使用,使文章具有独特的人情味,将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神形毕露,在启发读者想象的同时,也使文章更具生动性。
(四)排比
运用排比来讲述道理,会使文章条理清晰、脉络分明。运用排比来抒情,会使文章情感充沛,热情洋溢,节奏一致。运用排比来讲述事情、描绘道理,会使文章浅显的形象变得既深刻又细致。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14]不喜欢它(汉赋)的铺张,不喜欢它的富丽,不喜欢它的雕琢,不喜欢它的堆砌,不喜欢它的奇僻,当然,更不喜欢它的歌颂阿谀、不见风骨。[15]作者以排比来说理,则把道理阐述得更加严密、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对文人的评价显得淋漓尽致。
(五)反问
反问是只问而不答,在作品中既有质问之感,又能深化思想、加重语气。如果不分高低,只让每个时间和空间的民众自由取用、集体“海选”,那么,中国文学,能选得到那位流浪草泽、即将投水的屈原吗?能选得到受过酷刑、耻而握笔的司马迁吗?能选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艰苦躬耕的陶渊明吗?[16]以反问引起读者的重视和思考,发人深思,激发了读者的情感,而且使内容的表述深入,脉络清晰,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反问的使用使作品语气加强,增强了文中的气势,为作品奠定了慷慨激昂的情感基调。
(六)引用
作品善于利用硕士名儒的语言、观点,强化自己的语言,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支撑自己的观点,进而说明对待事物的新观点、新看法、新认识。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之为“艳若桃花”。[17]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我觉得,北魏就是一个历史支点,它撬起了唐朝。[18]这里引用大家比较熟悉、感兴趣的话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丰富而含蓄,简练而典雅,富有启发性,增强了语言的说服力。文中所使用的语言偶尔也会有些夸张,实则是为了加强论证的深刻性和具体性,并烘托了创作气氛,增强了读者的联想力,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也用重复的语言,突出了思想,强调了感情。《中国文脉》修辞方法的大量使用,使读者生动、形象地感受到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的气韵。我们慢慢翻开,细细品读,这一幅长长的画卷古色古香,沁人心脾。从中我们静听着《诗经》的旋律,秉承着先秦诸子的教诲,同情着屈原的愤懑,欣赏着盛唐诗歌的气魄,吟诵着婉约豪放的宋词,亲临着“红楼”台榭的绚烂……当然偶尔也有颜真卿、张旭等书法家的点缀,使这色彩缤纷的文学画廊又增添了几分新雅。
三、幽默的色彩文化的通俗
《中国文脉》在语言的运用上十分诙谐、幽默。既阐释了文学史的浩瀚无穷、博大精深,又能使读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过程中感受文化历史的魅力。同时,文中还采用了大量的现代流行词汇,时尚而富有感染力,老少皆宜,使遥远而陌生的文化历史缱绻而至在人们的面前。
(一)幽默诙谐
没有幽默的语言,如同一盘没有作料的凉菜,浅淡无味。品读《中国文脉》,读者会感到有滋有味。这里余秋雨突出幽默的趣味性,在评论、批判的同时偶有调侃,以看似平实的笔墨潜含着激趣和诙谐,这使严谨的文学史变得通俗、生动起来。虽语出诙谐,但其用意却极其严肃。总之,到了屈原,文脉已经健壮,被“政脉”和“世脉”深深觊觎,并频频拉拢。说“绑架”太重,就说“强邀”吧。[19]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李煜)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20]苏东坡也曾经与政治有较密切关系,但终于在“乌台诗案”后两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21]幽默诙谐的语言不仅突出“文学”对政治、世俗的影响,而且还能够以轻松、和谐的方式将文化加以阐述,随和亲近的同时,又不失庄重、威严。
(二)流行时尚
文中的幽默还表现为时尚的现代词语的运用。用一些现代流行的词汇讲解历史文化,打破了时空的距离,让读者走进中国文学历史的长廊中。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懵方言。[22]雅静的文脉,从此经常会被“政脉”、“世脉”的频频强邀……这种“静脉扩张”,对文脉而言有利有弊,弊大利小。[23]曹操的书记官阮瑀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接过了文脉。还算直接,却已有了悬崖峭壁般的“代购”。[24]这种景象(宋代文人当官),使文化和政治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高端联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为一体。[25]还有一些类似于“假大空”“征用”“打包”“转型”“指令”“品位”等等词语的使用,使文化历史的讲述由枯燥乏味变为生动有趣,由生疏遥远变为亲近和谐,由难懂拗口变为容易理解。幽默语言以及现代词汇的准确运用,使文中的议论、叙事、明理充满了智慧和趣味,使读者在理性的阅读和思考中得到一种别致、特殊的精神享受。读者从来没有读史学像读《中国文脉》这样,读得酣畅,读得淋漓,读得尽兴,读得尽情,爱不释手,反复体味。
四、诗歌的节奏文化的气韵
哲理性的思辨,雅俗共赏的语言,比喻、排比、对比等修辞方法的综合运用,使文章具有诗歌的节奏、诗歌的韵律、诗歌的美感,带给读者独特的享受。由于余秋雨深厚的古代文学修养,所以行文中常常给人一种沉浸于诗境的感觉。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再临。[26]于是,一部《红楼梦》,慰抚了五百年的荒凉。也许,辽阔的荒凉,正是为它开辟的仰望天空?因此,中国文脉悚然一惊,猛然一抖,然后就在这片辽阔的空地上站住了,不再左顾右盼。[27]锦绣斑斓的诗性语言,不是率尔操觚者所能想象的文字。凝练灵活的诗歌语言,显示出文章朗朗上口的节奏,悦耳动听,使中国文学的气脉气韵生动。因为余秋雨的价值观没有政治、民族、地域的功利限制,而是以公平的视野,站在高处俯瞰中国文学的发展,使得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气脉连贯,组成的坐标显得平衡而和谐。所以三千年的中国文脉在余秋雨的介绍中没有间断过,从先秦到现代气脉贯通,浑然一体。他用精准、典雅、华美、形象的语言,在中国文脉的长廊上,绘画出一个个耀眼的星座,使我们“从当代文化圈的吵闹和装扮中逃出,滤净心胸,腾空而起,静静地遨游于从神话到《诗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以及其他文学星座的苍穹之中。”[28]“成为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期盼者。”[29]
作者:冯常荣 孔鑫 单位:白城师范学院 汪清县春镇中学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