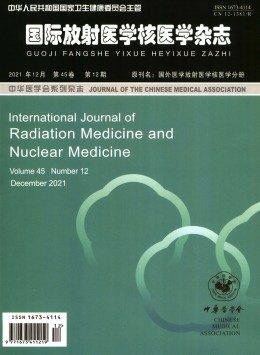医学科技人文职业风险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医学科技人文职业风险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1大部分医者认为医学人文是一只不下蛋的鸡
时下,很尴尬的是,医学人文在掌握了医学“硬”科技的医者身边“布道”时,常常会引致其充满鄙夷不屑的目光。其实,在不少医者的眼里,医学人文既不能杀灭病毒细菌逆转病情,也不能丰富医学科技层面的知识,更不能提升医疗专业技能;相比于“硬”技术,医学人文那玩意儿是或然的、边缘的、辅助的、几近无用的知识,是可有可无的职业情感训练[1]13。王一方先生在《医学是科学吗?》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其实大部分有医学知识背景的人都漠视医学人文学科,认为是一只‘不下蛋的鸡’……”[2]医学人文精神在当下的意义上几近为一种奢侈的理想。于是,医学科技转身向左,人文扭身向右,两者分道扬镳!
2医学人文精神被异化之关键词:强势、交易、遮蔽
先借用黑格尔在评价宗教改革时的一句话,“……他的心,他的灵魂在场”。实际上,医者一直“灵魂在场”,其所为之“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皆为医学之本真。人之为人,其身必为首要之根本。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第一位,精神第二位。身的物质属性无疑使其具有对心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是心之存在的基础与载体。人因患病而痛苦之时,对生理痛苦能立即解除的渴望,恐怕是患者的第一反应。于是,医学科技就需先从对患者的肉身干预入手。“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所以医者运用医学科技施治于被病痛折磨的患者,解除其肉体的痛苦,是医者对患者同情、悲悯情怀的彰显,这恰好生动地演绎了医学之灵魂的医学人文精神。医学何曾与其人文分开过?由此可见,“医学的人文是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给的。”[4]英国科学史专家斯蒂芬指出,医学是人道思想最早产生的领域,最初的医学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仁慈,一种人道关怀[5]。医学科技天然地具有内在的人文性,它被包含在医学人文之中,是医学人文的一个硬性的价值向度。
它以科学技术为利器,解除患者病痛,维系生命健康,是医学人文精神具体化、专业化、外在化形式,是医学人文精神实现的手段[6]。故而,医学科技与医学人文自医学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割裂过,医学的工具理性与医学的灵魂密不可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医学科技的进步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寿命男性71岁,女性74岁[7]。而1957年我国人均寿命才57岁[8]。生命权是人民权利的最好诠释,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在此,医学的人文精神得到了现实的诠释。在医学人文研究视域中,《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编辑部于2010年第7期开展了在医学人文知识建构方面的关于“好的医学”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但具有引导学界关注医学根源性问题的作用,而且还颇具导向性地规范医学人文研究路径起点的意义。因为当一种学科或学科群,定位了其研究的起点,拥有了自己的知识建构和研究路径时,其学术生命即为诞生,沿途而去,其力量则愈发彰显。在讨论中,王一方认为,从技术上看,医学(技术)“进步”(异化)是医学不可爱的真正根源。医者笃信科学这个“新教”的征服思想,崇拜技术的成长与成熟,技术主义甚嚣尘上,忽视对人类苦难的敏感、敬畏、同情和悲悯等职业情怀的养成。医者自身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我治病救人赖于科技之功,与人文何干?临床实践中,医者因掌握了医学科技而具有高贵感和优越感,患者寻求帮助是医者这个强者对弱者的恩典。医者表现为专制主义的职业傲慢、偏见与冷漠。对于疾病的诊疗,医者不愿、不会或不屑于与患者沟通专业技术方面的东西。如在医疗方案中,患者只需听话就成,即所谓“遵医嘱”。医者威严冷峻的权威态度,满嘴的专业术语,以及医患的交流媒介于冷冰冰的机器,更加深了与患者的鸿沟。
医学科技的强势,遮蔽了医学内在固有的人文内核,温情的医学不见了。从利益上看,物欲喧嚣下的交易格调是医者职业风险的经济诱因。医者瓜葛于各种利益集团,集团的利益胜过了患者的利益。而医者职业道德的净化机制还未健全,道德自律苍白,正确与正义,真理与真谛渐行渐远,越来越疏离[9]。同时,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财力与物力,而当财政的投入不断减少加之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之时,医者必定会把手伸向求助于他的患者。换言之,医疗卫生在当下中国极其强烈地表现为一种科技与金钱的交易模式了———你给我拿钱,我给你看病。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医患之间程式化的交易模式中渐渐消弭了。因此,强势的医学科技和交易格调的医患关系,遮蔽了医学科技内在固有的人文精神属性。医学的人文精神被异化,医学的人文关怀情愫,不见了。在民众的眼里医学“不可爱”了。于是,当患者肉体的病痛没能解除、精神的痛苦在医者的冷漠中加深以及金钱丧失等情况一并袭来之时,医患冲突的爆发达到了临界,剩下的就是导火索了[10]。如此,医者职业的风险危矣。
3哲学视角下的医者职业风险
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影响。近代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孤立、静止、片面地解释世界。在笛卡尔、斯宾诺莎所坚持的意识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二元论对立视角的哲学思维模式指导下,在科学技术提供的工具和手段帮助下,身心必然分离。“在机械唯物论影响下,医学就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11]。人,只剩下了肉身。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恩格尔教授正式提出了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新概念。但这种新的医学模式在当下中国的医疗卫生界并不“髦得合时”,大行其道的是生物医学模式。因为医者生活在具有深厚的、无比崇尚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在这种理念下,医者只需重视人的生理、病理属性即可。在他看来,患者来医院是因为病,要看病、治病,所以对准病才是正确的,谈别的都是虚妄、都是浮云。中国医疗卫生界在实践中的做派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患者到大医院看病,好不容易排队挂上号,但和医生说不上两句话,一大摞检查单已到眼前。接着是穿梭于钢筋混凝土之中,人若物品般毫无尊严可言地面对着不同的“质检”仪器的查验,然后换回报告单,再回医生处,医生盯着报告单,方子就开出来了。如此,哪里有什么医学新模式的影子?“建立在机械论基础上的医学模式将病因从神秘的天罚中拯救出来,最终将其交给了质料;将治疗从对上帝的敬畏与心灵的洗礼中解放出来,最终将其交给了物质的相互作用。”[12]
4医学人文精神异化的消解:医者职业风险的解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坐而哀叹、抱怨均于事无补,故而需刚健进取。笔者认为,要消解医学人文精神的异化,必须建基于维护和保障好医者和患者的利益与福祉,如此亦为化解医者职业风险之道。从对科技本身的直接规约来看,对医学科技的专业性几近无法制约。因为对于知识、经验、能力这类存在于人的头脑里的内在东西的规约,不同于对政治公权力的制约。或者说,洛克、孟德斯鸠等的政治权力制衡理论在对科技权力的约束中容易失效。其意义在于他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这种视角来看,消解医学人文精神的异化,只能从规约医者实施医疗技术的外在行为入手,所以各种各样的关于医疗卫生行为的制度法令出台就是必要的了。但仅有这些律令条例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执业医师法》只是刚性地规定了医学伦理学这一门课程是必考课程,其它“医学人文”类的学科不见踪迹。在以崇尚实用主义而著称的中国,在硬性的执业资格考试中必须再加入些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等“医学人文”类课程的考核。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特鲁多医生的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1]18它告诉医者,其职责不仅仅是诊疗和治愈,更多的是对患者的帮助和安慰。医学科学技术对很多疾病还是无能为力的。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为病人开出的成千上万种药物中,可有可无的占30%,基本无效的占60%,只有10%是确切有效的[11]。
因此,医者应保持一份理性的谦卑,常怀敬畏与尊崇生命之心,谨慎行医,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做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13]亦即医者当以此来力图张扬被遮蔽的医学人文精神,减少其与患者日甚一日的冲突,渐次化解自身的职业风险,构建和谐之医患关系。从利益的角度看。社会学家伦德尔•柯林斯指出,人们总是自我利益的追求者;人们在实现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与观念依赖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14]。人性是趋利的,道德的说教永远难以抵抗现实的利益诱惑;同时,道德也并非是高在云天的东西,它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所以,医疗卫生事业一日不能实现其公益性,医者的创收冲动就会存在一日。医者不去利用其专业技能的资源来掠取患者,他还能“宰”谁呢?姑且不论这种“宰”合理与否,眼前的实务是,患者不拿钱,就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医者没有钱也难以活下去,医院没有钱也就难以生存。没有了医者,没有了医院,何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医者纠结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中,实为一种无奈的生存之计。由此可见,对医学人文精神异化的消解,或者说对医者职业风险的解构,需要对过度市场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颠覆性的变革。可喜的是,医疗卫生体制正朝着公益化的方向迈进。笔者认为,医疗卫生体制的变迁,必须以刚性的执行为先决约束条件。如,保障医院公益性的财政补贴一定要及时足额到位。倘对医者的利益维护与保障不力,医者还必须“自劳自养”的话,那么无论社会上如何诟病医界,医者还必将继续扮演“白衣屠夫”的不良社会角色[15]。如是,医患之和谐仍将在山的那一边。
5结语
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陷于危机,而是失去反思的能力,因为没有反思就没有走出危机的可能。令人欣慰的是,医学人文研究者们正热烈地关注着医患冲突,他们不希望医者戴着钢盔去上班,也不希望请警察到医院看场子,更不希望白色的条幅横亘在医院的大门口,而是希望医学的灵魂日益得到彰显。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中深情地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笔者希冀,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应该是、也必须是一个最好的、充满着人文智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