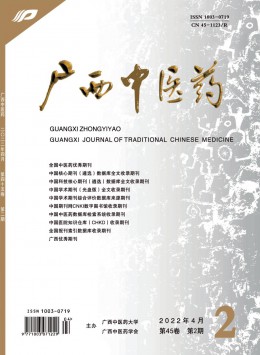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路径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路径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以中医药学为主体,融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与技术方法,创新中医药临床诊疗模式,丰富中医药理论体系,是现阶段中医药创新发展的一大重要方向。然而现代医学背景下的中医药传承创新工作还存在中医传统辨治模式与现代疾病临床诊疗难以有机融合、中医宏观辨治思路与现代医学微观理化指标不能精准对接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据此提出“两个重构”(即重构现代中医诊疗体系与重构现代中医本草体系)理论框架并对其内涵、目的、方法及意义进行了系统阐释。认为通过借鉴现代医学疾病认知,继承传统中医审病思维,对现代疾病进行中医的分类分期分证,进而可实现现代中医诊疗体系的重构;同时通过吸纳现代药理研究成果,融汇中药传统功效认识,构建方药量效理论框架推动现代中医本草体系的重构。“两个重构”的实现可在继承并发扬中医调态优势的前提下,突破传统辨证论治局限性,提高中医对现代疾病临床诊疗的精准性,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诊疗体系;本草体系;重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中医药创新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在现代医学背景下,基于诊断标准明确的现代疾病,面对患者改善疾病客观指标的迫切需求,如何在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传统优势的前提下,走好现代中医药创新发展道路,实现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互融互通、协调发展,是当代中医人面临的一道难题。为此我们创新性地提出了“两个重构”理论框架,即“重构现代中医诊疗体系”和“重构现代中医本草体系”[1],在保留传统中医宏观辨证与中药性味功效认知的基础上,突破传统辨证论治的局限性,提高中医临床辨治的精准性,搭建“病证结合”与“宏观微观结合”的两座中西医融合汇通之桥。本文将通过分析现代医学背景下,中医药创新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系统阐释实现“两个重构”的目的、方法及意义,以期为现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需要实现“两个重构”
1.1中医传统辨治模式与现代疾病临床诊疗难以有机融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它要求医者在充分获取四诊信息的基础上,运用八纲、六经、卫气营血等经典辨证方法来构建疾病某一阶段的“证”,进而确定治则治法并据此选方用药。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中医疾病诊疗模式使中医在调整患者整体功能状态、改善临床症状以及治疗一些病因不明、难以诊断的疾病时具有显著优势。但其突出的“刻下性”与“个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学对疾病全周期发展规律的认识及群体化诊治策略的制定。目前中医学对许多现代疾病的认识仍然不足,突出表现在中医疾病命名方面规范性不够。临床上,“病”“证”“症”互相通用、混杂不清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咳嗽”“头痛”既可以是症状又可以是病名,这也使得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之间难以实现直接对接,最后导致一个中医病名可以对应多个西医疾病、一个西医疾病可隶属多种中医病名的情况[2]。因此,对于接受传统中医辨病辨证诊疗体系教育的中医从业者而言,面对现代医学明确诊断的疾病,若不考虑西医诊断,直接辨证论治,则只能着眼当下患者表现的症状,而忽视对疾病发展的动态把握和整体防治;或虽考虑西医疾病诊断,在传统中医疾病认识体系中又难以找到能与现代疾病直接对应的中医药防治方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部分医者选择直接将西医临床诊断机械套用中医病名,如将“糖尿病”等同于“消渴”,将“冠心病心绞痛”等同于“胸痹”,从而试图将传统病名下中医药防治相关疾病的思路和方法移植到所对应现代疾病的诊疗中,尝试建立中西医之间的对应渠道。但因为只是截取了现代疾病某一发展阶段来进行中西医的机械对应,尚不能完全体现出疾病的整体发展规律和防治思路,因而难以系统化地指导现代疾病的中医治疗。因此,要想实现中医学创新发展,使“古方”可以治“今病”,必须吸纳现代医学疾病认知,突破中医传统辨治模式的局限,运用中医思维重新认识现代疾病并建立新的现代中医诊疗体系。
1.2中医宏观辨治思路与现代医学微观理化指标难以精准对接
“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另一特点。一直以来,中医学都强调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利用药物的偏性调整患病人体的偏态,通过调动人体的自调节、自修复、自平衡的能力,起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作用,此即“宏观调态”[3]。这一理念也是中医辨治的优势所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对机体结构、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层面已逐渐由宏观走向微观,影像、生化、免疫、病理等微观指标逐渐替代宏观的临床症状,成为许多疾病诊断和疗效判定的标准。单纯从宏观调态入手的中医治疗,往往不能对微观指标起到直接调整的作用,这也导致临床中医师在治疗一些早期以指标异常为突出表现的疾病或者面对疾病的典型病理指标时,感到临床选方用药没有抓手,宏观辨证难以精准起效。对此,沈自尹教授首先提出了“微观与宏观辨证结合模式”[4],强调在临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将现代医学的理化检查、超声、影像等检查结果作为辨证的依据,进而延伸传统中医四诊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丰富了中医辨证的内涵。辨证论治的最终目的在于寻求与治疗相对应的方药[5]。目前传统的中药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认识仍然依托于宏观的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以改善疾病的症状和证候为目标,难以适配微观理化指标诊疗的临床应用场景,传统方药与现代指标之间尚缺乏直接的药理和药效关系。故而需要重新构建现代中医本草体系,探索中药的微观治疗靶点,丰富传统本草认知,以支持真正“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证-治-方-药-效”一体化辨治。
2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如何实现“两个重构”
中医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要打破传统诊疗模式,推进改革创新,绝非易事。应在充分继承和发扬传统优势的同时实现诊疗体系和本草体系的重构,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
2.1重构现代中医诊疗体系,突破传统疾病认知
2.1.1借鉴现代医学疾病认知,全面把握疾病发展规律
突破中医传统疾病认识,需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对于现代医学已研究的较为深入和成熟的疾病,应充分借鉴吸纳其临床诊断方法与群体化研究成果,立足中医思维方法,对疾病进行全程、全面的再认识,厘清疾病发展规律,深化中医疾病认识,以弥补中医传统诊疗模式的不足。以糖尿病为例,古人观察到此类患者以多食、多饮、多尿、消瘦症状为特点,因此命名为“消渴”。然而,一方面,存在“消渴”症状的疾病还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尿崩症等,其治疗方法与糖尿病截然不同;另一方面,现代糖尿病的诊断以血糖水平为准,诊疗手段的进步使现代糖尿病的确诊时间较古代消渴大大提前。大样本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已证实,处在糖尿病早中期的患者多以实证的肥胖、超重为主[6],而消渴病机多强调“气阴亏虚”,故以消渴论治糖尿病仅能覆盖糖尿病中晚期的病机特点。同时,现代病理研究已充分表明,糖尿病自发病起即存在对血管、神经的损害,若没有及时干预,久病入络,络损及脉,后期将出现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等多种神经血管并发症[7],但目前中医临床仍主要将这一病变归属消渴之后的并病阶段,使得中医药失去了早期干预的先机。因此,改变糖尿病与“消渴”直接对应的机械认识,借鉴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知,运用中医思维,重新全面审视并把握糖尿病的中医病变规律迫在眉睫。
2.1.2继承传统中医审病思维,充分突出宏观调态优势
借鉴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并不意味着抛弃中医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更应该在充分挖掘经典古籍,传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守正创新,融汇新知,用中医思维方式重新认识现代疾病并用中医药术语重新进行论述。如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SARS)命名为“肺毒疫”[8],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命名为“寒湿疫”[9],二者均属烈性传染病故以“疫”名之,前者强调了病位和病机,后者则突出了病邪性质。又如将糖尿病命名为“糖络病”,“糖”即血糖升高,“络”即络脉损伤,强调了糖尿病中医治疗当全程贯穿降糖治络的思想[10]。由此可见,通过对现代疾病重新进行中医赋名,不仅可以使其中医病理病机一目了然,同时也有助于临床工作者把握疾病的中医辨治要点。此外,依据现代疾病病理演变规律对疾病重新进行中医的“分类分期分证”也是重构中医诊疗体系的重要途径[11]。所谓分类,乃根据患者表现的不同临床特点对疾病进行横向的亚型区分,这种区分可能来源于现代的临床认知,也可能启发于古人的经验总结,其最终目的是区别不同病理特点的患者,使治疗更具有针对性;所谓分期,则是对疾病全程的不同阶段从时间轴上纵向区分,通过抽提疾病发展各阶段的中医核心病机要素,实现对疾病时空变化规律的把握。分类分期后,患者所处的阶段及病因、预后已经明了。以此为基础,再进行各阶段的分证施治,在发挥中医宏观调态优势的同时“先安未受邪之地”,实现对疾病下一步演变的预防。如本团队以《黄帝内经》脾瘅、消瘅作为理论依据,将“糖络病”分为胖型(脾瘅)和瘦型(消瘅)两类,并总结疾病核心病机演变规律,将糖尿病前期、早期、中期和并发症期总结为郁、热、虚、损四态,在“早期治络、全程治络”基础上,分别总结各阶段证候类型并予以辨证施治,以此为糖尿病重新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医理论的诊疗体系,从横向(分类、分证)和纵向(疾病发展时间轴)把握全局,实现对疾病的全面认识[12]。
2.2重构现代中医本草体系,实现中医精准打靶
2.2.1吸纳现代药理研究成果,融汇中药传统功效认识
要提高中药对微观指标如临床理化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的靶向性,需要寻找“标靶”药,即可以针对性改善现代临床指标的中药,这样的药物功效认识,古籍难觅,唯向今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组织开展了大量的中药药理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青蒿素等中药单体被人们提取和认知,许多中药的现代药理、药效作用也逐渐明晰。这些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为寻找中医临床“标靶”药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但是,中药的使用首先应当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因此重构现代中医本草体系强调要将中药药理研究成果回归中医思维,整合中药药理靶点与中医传统药性理论,丰富并完善中药的现代认知,使本草同时拥有宏观的药性功效属性与微观的药理靶点属性(即态靶同调性),以便提高临床选方用药的靶向性和精准度,同时也有助于验证中药药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例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桑叶、黄连、知母等中药的主要成分均具有良好的降糖效果[13],其中桑叶取自树梢,为轻清之品,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平抑肝阳等功效,恰合糖尿病“郁态”阶段患者肝气不舒、上焦郁热的特点;而黄连归肝、胃、大肠经,可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故尤适用于“热态”阶段辨证为肝胃郁热、胃肠实热、肠道湿热证的患者;但若患者病程较长进入糖尿病“虚态”阶段,此时火热耗伤津液,导致气阴两虚,脏腑经络失于濡养,出现口渴多饮、多食、多尿的“三消”症状,则可选用知母、生地黄、天花粉等甘寒之品,在滋阴清热的同时起到降糖止渴的作用[13],如此便可实现中医“态靶同调”的精准治疗。
2.2.2构建方药量效理论框架,实现临床药物精准用量
王清任《医林改错》言:“药味要紧,分量更要紧”。剂量是中医临床在确定理、法、方、药后影响疗效的关键因素。但目前中医方药量效理论缺乏系统研究、内涵模糊,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价值有限,也制约了方药的有效开发及其产业化发展[14]。因此除了药物功效靶点的精准认知外,“量-效”研究也是重构本草体系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只有精准的方药剂量才能带来精准的疗效。在这一点上,古人实则已积累了上千年的用药经验,需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历代中医临床用药经验,深入挖掘和考据经典方剂的临床剂量范围和剂量使用特点,并通过现代临床研究手段,结合药理、药效学等现代研究技术,探索中药最佳剂量范围,阐释中药量-效规律。例如,本团队系统考证了《伤寒论》本源剂量,确证了经方本源剂量为一两等于13.8g[15],并按此剂量分别选取代表性“急、危、重、难”四大类疾病开展临床研究。通过文献考据、药物实测、重量比例、煎煮提取及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分析等方法,最终提出经方1两在急危重难疾病中约折合9g,而在普通疾病治疗中可折合6g,调理性或预防性用药则可按3g折算,为中药的临床合理应用提供了依据[16]。
3结语
受时代条件所限,古代中医想要对一类疾病进行几十年的长期观察非常困难,群体性的资料则更加匮乏。如今,现代医学对疾病发病规律的研究,以及中医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内科分科诊疗,让中医学能有条件对许多现代疾病尤其是慢性病进行完整、系统的诊疗研究,为现代中医诊疗体系的重构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与此同时,先进的现代科技手段带来了对疾病和医药的微观化认识,中药药物成分、代谢过程和作用机制的揭示,也让现代中医本草体系的重构成为了可能。时至今日,中医与现代医学的碰撞交流已走过了百年岁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通过“两个重构”,我们可以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医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汲取现代医药学研究成果,从中医药角度,对现代疾病重新进行系统的理法方药量的认知,为形成中国特色的中西医融合的新医学奠定基础,开辟道路。
参考文献
[1]宋珏娴,傅晓燕,仝小林.现代医学背景下中医诊疗体系的重构[J].中医杂志,2018,59(1):6-9.
[2]魏佳,李灿东.中医病名规范化研究现状与对策[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3):1217-1220.
[3]仝小林,何莉莎,赵林华.论“态靶因果”中医临床辨治方略[J].中医杂志,2015,56(17):1441-1444.
[4]沈自尹.微观辨证和辨证微观化[J].中医杂志,1986(2):55-57.
[5]宋美芳,陈家旭,彭晨习,等.论中医微观辨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7):2867-2869.
[6]魏军平,刘芳,周丽波,等.北京市糖耐量异常和糖尿病危险因素及中医证候流行病学调查[J].北京中医药,2010,29(10):731-737.
[7]仝小林.中医肺毒疫辨识[J].中医杂志,2003,53(12):885-887.
[8]仝小林,李修洋,赵林华,等.从“寒湿疫”角度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药防治策略[J].中医杂志,2020,61(6):465-470,553.
[9]郑玉娇,苟筱雯,逄冰,等.“糖络病”学说及其诊疗要点发微[J].中医杂志,2019,60(22):1920-1923.
[10]王翼天,仝小林.分类、分期、分证思想对慢性病中医理论构建的启示[J].中医杂志,2017,58(24):2091-2094.
[11]仝小林,刘文科,王佳,等.糖尿病郁热虚损不同阶段辨治要点及实践应用[J].吉林中医药,2012,32(5):442-444.
[12]苟筱雯,赵林华,何莉莎,等.从态靶辨证谈中医治疗2型糖尿病的用药策略[J].辽宁中医杂志,2020,47(4):1-4.
[13]仝小林,王跃生,傅延龄,等.方药量效关系研究思路探讨[J].中医杂志,2010,51(11):965-967.
[14]傅延龄,宋佳,张林.经方本原剂量研究的意义[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4):231-233.
作者:丁齐又 赵林华 宋斌 雷烨 杨映映 张博荀 张伟 胡诗宛 仝小林 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遵义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甘肃中医药大学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